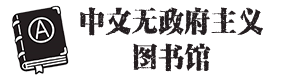CrimethInc.
从民主到自由
民主是当今最普遍的政治理想。乔治·布什援引它来为入侵伊拉克辩护;奥巴马祝贺解放广场的叛军将它带到埃及;“占领华尔街”运动声称已经提炼出了它的纯粹形式。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到罗贾瓦自治区,几乎每一个政府和人民运动都自称是民主的。
解决民主问题的方法是什么?每个人都同意:更民主。自世纪之交以来,我们看到了大量的新运动,承诺提供真正的民主,与他们所描述的排他性、强制性和疏离性的表面民主制度形成鲜明对比。
是否有一条共同的主线将所有这些不同类型的民主联系起来?哪一个是真的?他们中的任何一个能带来我们与这个词联系在一起的包容和自由吗?
受直接民主运动经验的驱使,我们回到了这些问题上。我们的结论是,导致人们从纽约到萨拉热窝走上街头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巨大不平衡,并不是特定民主国家的偶然缺陷,而是可以追溯到民主起源本身的结构特征;它们几乎出现在古往今来的每一个民主政府的例子中。代议制民主保留了所有最初为国王服务的官僚机构;直接民主倾向于在更小的范围内重建它,甚至在国家的正式结构之外。民主并不等同于自决。
可以肯定的是,许多好的事情经常被描述为民主的。这并不是反对讨论、集体、集会、网络、联盟或与你不总是同意的人合作的论点。相反,我们的论点是,当我们参与这些实践时,如果我们理解我们所做的是民主——作为一种参与式政府的形式,而不是自由的集体实践——那么迟早,我们会重现与不那么民主的政府形式相关的所有问题。这适用于代议制民主和直接民主,甚至适用于协商一致的过程。
与其将民主程序本身作为目标,不如让我们回到当初引导我们走向民主的价值观:平等主义、包容,以及每个人都应该掌握自己命运的理念。如果民主不是实现这些目标的最有效方式,那么什么才是?
随着越来越激烈的斗争冲击着当今的民主国家,这场讨论的利害关系也越来越大。如果我们继续试图用一种更具有参与性的方式来取代现有的秩序,我们就会回到起点,而其他和我们一样幻灭的人会被更专制的选择所吸引。我们需要一个能够兑现民主所背弃的承诺的框架。
在接下来的文本中,我们将研究连接不同形式民主的共同线索,追溯民主的发展,从其古典起源到当代的代表性、直接性和基于共识的变体,并评估民主话语和程序如何为采用它们的社会运动服务。在此过程中,我们概述了直接而非通过民主统治寻求自由意味着什么。
这个项目是多年跨大陆对话的结果。作为补充,我们发表了被宣传为直接民主典范的运动参与者的案例研究:西班牙5月15日运动(2011年)、希腊占领宪法广场运动(2011年)、美国占领运动(2011 - 2012年)、斯洛文尼亚起义(2012-2013年)、波斯尼亚全体会议(2014年)和罗贾瓦革命(2012-2016年)。
什么是民主?
民主到底是什么?大多数教科书上的定义都与多数决定原则或民选代表政府有关。另一方面,一些激进分子认为,“真正的”民主只发生在外部,反对国家对权力的垄断。我们应该把民主理解为一套具有特定历史的决策程序,还是一种对平等主义、包容和参与性政治的普遍愿望?
“什么是民主?”
“嗯,我自己也不太清楚。就像所有其他类型的政府一样,我相信这与年轻人互相残杀有关。”
——《约翰尼有枪》(1971)
为了确定我们批判的对象,让我们从术语本身开始。民主一词来源于古希腊语dēmokratía,由dêmos“人民”和krátos“权力”组成。这种人民统治的提法在拉丁美洲重新流行起来,它回避了一个问题:哪些人?什么样的权力?
demos和kratos这两个词根暗示了所有民主的两个共同特征:一种决定谁参与决策的方式,一种执行决策的方式。换句话说,公民身份和治安。这些是民主的基本要素;正是他们使它成为一种政府形式。除此之外,更恰当的说法是无政府主义——政府的缺失,源自希腊语an-“没有”和arkhos -“统治者”。
民主的共同特征:
一种决定谁参与决策的方法
(demos)
一种执行决策的方式
(kratos)
一个合法决策的空间
(polis)
以及维持它的资源
(oikos)
谁有资格成为demos?有些人认为,从词源学上讲,demos从来不是指所有人,而是指特定的社会阶层。尽管民主的支持者鼓吹其所谓的包容性,但在实践中,民主总是要求一种区分包容和排斥的方式。这可能是立法机构的地位、投票权、公民身份、会员资格、种族、性别、年龄或街头集会的参与情况;但在任何形式的民主中,要有合法的决定,就必须有合法的正式条件,以及一群明确的人来满足这些条件。
在这方面,民主使其起源于希腊的狭隘的沙文主义特征制度化,同时它似乎提供了一种可以涉及全世界的模式。这就是为什么民主被证明与民族主义和国家如此相容;它以他者为前提,他者不被赋予同样的权利或政治代理。
在卢梭颇具影响力的《社会契约论》(of The Social Contract)一书中,对包容和排斥的关注在现代民主的曙光中已经足够清晰,他在书中强调,民主和奴隶制之间并不矛盾。他认为,越多的“恶人”被铐在镣铐里,公民的自由就越完美。正如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后来所说,狼的自由就是羔羊的死亡。在这个比喻中所表达的自由的零和概念是国家授予和保护权利话语的基础。换句话说:为了让公民获得自由,国家必须拥有最高权力和实施全面控制的能力。国家试图生产绵羊,而为自己保留狼的地位。
相比之下,如果我们将自由理解为累积的,那么一个人的自由就变成了所有人的自由:这不仅仅是一个受到当局保护的问题,而是以一种使每个人的可能性最大化的方式相互交叉的问题。在这个框架中,强制性越集中,自由就越少。这种理解自由的方式是社会性的,而不是个人主义的:它将自由视为一种集体产生的与我们潜力的关系,而不是私人权利的静态泡沫。[1]
让我们转向另一个词根,kratos。民主与贵族政治、专制政治、官僚主义、财阀政治和技术官僚政治共享这个后缀。这些术语都描述了由社会的一部分人管理的政府,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逻辑。这条主线就是kratos,权力。
什么样的权力?让我们再一次向古希腊人请教。
在古希腊,每一个抽象的概念都有一个神的化身。奎托斯(kratos)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泰坦巨人,体现了与国家权力相关的强制力量。奎托斯出现的最古老的来源之一是戏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由埃斯库罗斯在雅典民主早期创作。该剧以奎托斯强行护送被铐着的普罗米修斯开场,普罗米修斯因为从众神那里偷火给人类而受到惩罚。奎托斯以一个狱卒的形象出现,不加思考地执行着宙斯的命令——一个“为任何暴君的行为而生”的野蛮人。
奎托斯所代表的那种力量是民主与专制和其他任何形式的统治的共同之处。他们共享强制制度:法律机构、警察和军队,所有这些都先于民主,并一再超越民主。这些工具是“为任何暴君的行为而制造的”,无论掌舵的暴君是国王、官僚阶层还是“人民”本身。正如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所说:“民主仅仅意味着人民为了人民而用人民的棍棒打击人民。”一个世纪后,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er al Gaddafi)不无讽刺地附和道:“民主就是人民监督人民。”
在现代希腊语中,kratos只是国家的意思。要理解民主,我们必须更仔细地审视政府本身。
“按照众所周知的中央集权和民主的平衡,实行民主和合法的中央行政控制并不矛盾……民主巩固人民之间的关系,它的主要力量是尊重。”来自民主的力量要求更高程度的坚持,以极大的准确性和热情执行命令。”
——萨达姆·侯赛因,《民主:个人和社会力量的源泉》
垄断的合法性
“正如在专制政府中,国王就是法律一样,在自由国家中,法律应该是国王。”
——托马斯·潘恩,《常识》
作为一种政府形式,民主提供了一种方法,可以从各种各样的欲望中产生一种单一的秩序,将少数人的资源和活动纳入多数人制定的政策中。在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都有一个合法的决策空间,与生活的其他部分不同。它可以是议会大楼里的大会,也可以是人行道上的大会,或者是通过iPhone拉票的应用程序。在任何情况下,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不是我们的迫切需要和欲望,而是特定的决策过程和协议。在一个国家,这被称为“法治”,尽管这一原则并不一定需要正式的法律体系。
这就是政府的本质:在一个空间做出的决定决定了在所有其他空间可以发生的事情。结果就是异化——决定的东西和现实的东西之间的摩擦。
民主承诺通过将每个人纳入决策空间来解决这个问题:所有人的统治。“民主国家的公民服从法律,是因为他们认识到,无论间接地如何,他们是在服从自己作为法律制定者的身份。”但是,如果所有这些决定实际上都是由它们所影响的人做出的,那么就没有必要通过某种方式来执行它们。
“最大的困难在于:你必须首先使政府能够控制被统治者;其次,还要迫使它控制自己。”
——詹姆斯·麦迪逊,《联邦党人》
在这个赢家通吃的体系中,是什么保护了少数群体?民主倡导者解释说,少数群体将受到制度条款的保护,即“制衡”。换句话说,控制他们的权力结构应该保护他们不受自己的伤害。[2]在这种方法中,民主和个人自由从根本上被认为是矛盾的:为了保护个人的自由,政府必须能够剥夺每个人的自由。然而,相信机构将永远比维护它们的人更好,确实是乐观的。我们赋予政府越多的权力,希望保护边缘群体,当它变成对他们不利的时候,就会变得越危险。
你在多大程度上相信民主进程应该胜过你自己的良心和价值观?让我们做个快速练习。想象你身处一个有奴隶的民主共和国——比如,古雅典,古罗马,或者1865年底前的美利坚合众国。你会遵守法律,视人民为财产,同时努力改变法律吗?你完全清楚,与此同时,整整几代人都可能在枷锁中生老病死?还是会像哈丽特·塔布曼和约翰·布朗那样,凭良心行事,无视法律?
如果你愿意追随哈丽特·塔布曼(Harriet Tubman)的脚步,那么你也会相信有比法治更重要的东西。这是一个问题,任何人都想使符合法律或多数人的意志成为合法性的最终仲裁者。
“难道不能有这样一个政府,在这个政府中,实际上不是由大多数人,而是由良心来决定是非吗?”
——亨利·大卫·梭罗《论公民的不服从》
最初的民主
在被大肆吹捧为“民主诞生地”的古雅典,我们已经看到了从那时起一直是民主政府的基本特征的排斥和强制。只有受过军事训练的成年男性公民才能投票;妇女、奴隶、欠债者以及所有没有雅典血统的人都被排除在外。民主最多只涉及不到五分之一的人口。
事实上,古代雅典的奴隶制比其他希腊城邦更为普遍,女性相对于男性拥有更少的权利。男性公民更加平等显然意味着更加团结起来反对妇女和外国人。参与政治的空间是一个封闭的社区。
我们可以在雅典的对立中描绘出这个封闭社区的边界在公共和私人之间在城邦和贵族之间。希腊城邦城邦是一个公共话语的空间,公民平等互动。相比之下,oikos,即家庭,是一个等级空间,男性财产所有者统治至高无上——这是政治范围之外的区域,但却是政治的基础。在这种二分法中,oikos代表了为维持政治提供资源的一切,但却被理所当然地视为先于政治,因此在政治之外。
这些分类今天仍然存在。“政治”(“城市事务”)和“警察”(“城市管理”)这两个词来自于城邦,而“经济”(“家庭管理”)和“生态”(“家庭研究”)则来自于oikos。
民主仍然以这种分裂为前提。只要公共和私人之间存在政治上的区别,从家庭(以无形和无偿劳动维持主流秩序的性别亲密空间)[3]到整个大陆和民族(如殖民时期的非洲——甚至黑人本身),一切都可能被排除在政治领域之外。同样,财产制度及其所产生的市场经济,自民主起源以来一直是其子结构,在被政治机器强制执行和捍卫的同时,也被置于不容置疑的地位。
幸运的是,古代雅典并不是平等主义决策的唯一参照点。对其他社会的粗略调查揭示了许多其他的例子,其中许多都不是基于排他性或强制。但我们是否也应该把这些国家理解为民主国家?
"难道我们应该相信,在雅典人之前,任何人,任何地方,都从未想过,把他们社区的所有成员聚集在一起,以一种给每个人平等发言权的方式共同做出决定吗"
——大卫·格雷伯,《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碎片》
在《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碎片》一书中,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让他的同事们把雅典确定为民主的起源;他推测易洛魁人、柏柏尔人、苏拉维齐人或塔伦西人的模型之所以没有受到那么多的关注,仅仅是因为它们都没有以投票为中心。一方面,格雷伯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那些专注于建立共识而不是实行强制的社会,这是正确的:其中许多社会比古代雅典更能体现与民主有关的最佳价值观。另一方面,我们给这些例子贴上真正民主的标签,同时质疑发明这个词的希腊人的民主资格,这是没有意义的。这仍然是一种种族中心主义:在我们自己公认的低劣的西方范式中,通过授予非西方榜样荣誉地位来肯定它们的价值。相反,让我们承认,民主作为一种可以追溯到斯巴达和雅典并在世界范围内被效仿的特定历史实践,并没有达到许多其他社会所设定的标准,将它们描述为民主是没有意义的。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来描述和尊重他们,会更负责任,也更准确。
毕竟,雅典是民主制度的始祖。如果雅典变得如此有影响力,不是因为它有多自由,而是因为它如何利用参与性政治来控制国家的权力呢?当时,人类历史上的大多数社会都是没有国家的;有些是等级制的,有些是水平的,但没有一个无国家的社会拥有奎托斯的中央集权。相比之下,现存的国家几乎谈不上平等主义。雅典人创新了一种混合形式,在这种形式中,横向与排斥和强制相结合。如果你理所当然地认为这种状态是可取的,或者至少是不可避免的,这听起来很有吸引力。但如果国家是问题的根源,那么古代雅典的奴隶制和父权制并不是民主模式的早期违规行为,而是从一开始就编码在其DNA中的权力失衡的迹象。
代议制民主——权力市场
与雅典相比,美国政府与古罗马共和国的相似之处更多。罗马公民不是直接管理,而是选举代表来领导一个复杂的官僚机构。随着罗马领土的扩张和财富的涌入,小农失去了立足之地,大量被剥夺财产的人涌入首都;动荡迫使共和国将投票权扩大到越来越多的人群,然而政治包容并没有抵消罗马社会的经济分层。这一切听起来似曾相识。
罗马共和国在尤利乌斯·凯撒夺取政权后走向灭亡;从那时起,罗马由皇帝统治。然而,对于普通罗马人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官僚机构、军队、经济和法院继续像以前一样运作。
“那些相信民主和君主制之间有明显区别的人,很难理解一个政治机构如何能经历如此多的变革而保持不变。然而,只要一眼就能看出,在英国君主政体的所有演变过程中,随着它的扩张和革命,甚至随着它跨越海洋成为一个殖民地,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然后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同样的国家职能和态度基本上没有改变。”
—伦道夫·伯恩,《国家》
快进到18世纪的美国独立战争。大英帝国的北美臣民对“无代表的税收”感到愤怒,他们反抗并建立了自己的代议制民主制度,很快就建立了罗马式的参议院。[4]然而,国家的职能再一次没有改变。那些为推翻国王而斗争的人发现,有代表权的税收并没有什么不同。结果是一系列起义——夏伊叛乱、威士忌叛乱、弗莱斯叛乱等等——都被残酷镇压。新的民主政府成功地安抚了大英帝国失败后的人民,这要归功于许多反抗国王的人的忠诚:因为这个新政府不代表他们吗?[5]
这个故事被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在1848年的法国革命中,临时政府的警察局长进入了国王的警察局长空出来的办公室,拿起了他的前任刚刚放下的文件。在20世纪的希腊、西班牙和智利,以及最近的突尼斯和埃及,从独裁到民主的过渡中,推翻独裁者的社会运动不得不继续与民主政权下的警察进行斗争。这就是奎托斯,也就是一些人所说的“深层国家”(Deep State),从一个政权延续到下一个政权。
法律、法院、监狱、情报机构、税务人员、军队、警察——大多数我们认为在君主制或独裁统治下具有压迫性的强制权力工具,在民主制度下也是如此。然而,当我们被允许投票决定谁来监督它们时,我们就应该把它们视为我们的,即使它们被用来对付我们。这是两个半世纪民主革命的伟大成就:他们没有废除国王统治的手段,而是让这些手段变得受欢迎。
“制宪会议是特权阶级在不可能实行专政的情况下用来防止革命的手段,或者在革命已经爆发的情况下,以使革命合法化为借口来阻止革命的进展,并尽可能地收回人民在起义期间取得的成果的手段。”
——埃里科·马拉泰斯塔,“反对制宪会议就是反对独裁”
自美国独立战争以来,权力从统治者向议会的转移过早地中止了革命运动。反叛者没有通过直接行动实现他们所追求的变革,而是将这一任务托付给了他们执掌国家的新代表,结果却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梦想被出卖。
国家确实很强大,但有一件事它不能做,那就是为它的臣民提供自由。它不能,因为它的存在是从他们的臣服中得来的。它可以征服他人,它可以征用和集中资源,它可以征收税款和义务,它可以发放权利和让步——这是被统治者的安慰奖——但它不能提供自决。奎托斯可以统治,但不能解放。
相反,代议制民主承诺了轮流统治彼此的机会:一种分散的、临时的王权,就像股票市场一样分散、动态,但又有等级。在实践中,由于这一规则是委托的,仍然有统治者相对于其他人拥有巨大的权力。通常,像布什和克林顿一样,他们来自事实上的统治阶级。这个统治阶级倾向于占据我们社会中所有其他等级的上层,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即使一个政治家是在平民中长大的,他越行使权力,他的利益就越偏离被统治者的利益。然而,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政客的意图;它是国家本身的机器。
在争夺指导国家强制权力的权利时,参赛者从不质疑国家本身的价值,即使在实践中他们只是发现自己处于国家力量的接收端。代议制民主提供了一个压力阀:当人们不满意时,他们将目光投向下一次选举,认为国家本身是理所当然的。的确,如果你想制止企业牟取暴利或破坏环境,难道国家不是唯一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的工具吗?不要在意,是国家首先建立了这些可能发生的条件。
“自由选举主人并不会废除主人或奴隶。在各种各样的商品和服务中自由选择并不意味着自由,如果这些商品和服务维持了对艰辛和恐惧生活的社会控制——也就是说,如果它们维持了异化。个体自发地复制叠加的需求并不能建立自主性;它只是证明了控制的有效性。”
——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
民主和政治不平等到此为止。那么从民主诞生之初就伴随着的经济不平等呢?你可能会认为基于多数决定原则的制度会缩小贫富差距,因为穷人占多数。然而,就像古罗马时代一样,与当前民主的优势相匹配的是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巨大鸿沟。这怎么可能呢?
就像资本主义在欧洲取代了封建制度一样,代议制民主被证明比君主制更具可持续性,因为它在国家的等级制度中提供了流动性。美元和选票都是一种等级分配权力的机制,可以减轻等级制度本身的压力。与封建时代的政治和经济停滞相反,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不断地重新分配权力。由于这种动态的灵活性,潜在的反叛者更有可能提高自己在现行秩序中的地位,而不是推翻它。因此,反对派倾向于从内部重振政治制度,而不是威胁它。
代议制民主之于政治,犹如资本主义之于经济。消费者和选民的愿望被货币所代表,这些货币承诺赋予个人权力,但却无情地将权力集中在社会金字塔的顶端。只要权力集中在那里,就很容易阻止、收买或消灭任何威胁到金字塔本身的人。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当有钱有势的人看到他们的利益受到民主制度的挑战时,他们能够搁置法律来解决问题——看看古罗马的格拉古兄弟和现代智利的萨尔瓦多·阿连德的可怕命运吧。在国家的框架内,财产总是胜过民主。[6]
“在代议制民主中,就像在资本主义竞争中一样,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但只有少数人能脱颖而出。如果你没有赢,那一定是你不够努力!这同样是为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辩护的理由:看,你们这些懒汉,如果你们更努力一点,就可以成为比尔·考斯比或希拉里·克林顿。但是,无论我们多么努力工作,都没有足够的空间来容纳我们所有人。
当现实是通过媒体产生的,而媒体的访问是由财富决定的,选举只是广告活动。市场竞争决定了哪些游说者获得资源来决定选民做出决定的依据。在这种情况下,政党本质上是提供立法投资机会的企业。当政治代表直接依赖他们的客户获得权力时,指望他们反对客户的利益是愚蠢的。”
——工作
直接民主:没有国家的政府?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现在。非洲和亚洲正在见证新的民主运动;与此同时,在欧洲和美洲,许多人对代议制民主的失败感到失望,他们把希望寄托在直接民主上,从罗马共和国模式转向了雅典的前身。如果问题在于政府对我们的需求反应迟钝,那么解决办法难道不是让政府更具参与性,让我们直接行使权力,而不是把权力委托给政客吗?
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对法律而不是立法者投票吗?或者推翻现行政府,建立一个联邦政府?还是别的什么?
“真正的民主只存在于人民的直接参与,而不是通过他们的代表的活动。议会一直是人民和权力行使之间的法律障碍,它将群众排除在有意义的政治之外,并垄断了他们的主权。人们只剩下表面的民主,这体现在投票时排长队。”
——穆阿迈尔·卡扎菲《绿皮书》
一方面,如果直接民主只是一种更具参与性和耗时的方式来控制国家,它可能会让我们在政府的细节上有更多的发言权,但它将保留其固有的中央集权。这里有一个规模问题:我们能想象2.19亿合格选民直接参与美国政府的活动吗?传统的答案是,地方议会将派代表到地区议会,而地区议会将派代表到全国议会——但是,在那里,我们又在谈论代议制民主。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想象,由高层下令举行一系列无休止的公民投票,以取代定期选举代表。
这一愿景最有力的版本之一是由海盗党等组织推动的数字民主或电子民主。海盗党已经被纳入现有的政治体系;但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想象人们通过数字技术联系在一起,通过实时多数投票来做出有关他们社会的所有决定。在这样的秩序下,多数政府将获得几乎不可抗拒的合法性;然而,最大的权力可能会集中在管理这一体系的技术官僚手中。通过对算法进行编码,决定哪些信息和哪些问题会出现在前面,它们将比今天的选举年广告更具一千倍侵入性地塑造参与者的概念框架。
“将世界简化为代表性的数字项目与选举民主的计划相一致,在选举民主中,只有通过规定的渠道行事的代表才能行使权力。两者都反对一切不可计算和不可简化的东西,把人类安置在一张普罗克洛斯蒂斯式的床上。作为电子民主的融合,它们将提供对大量细节进行投票的机会,同时使基础设施本身毫无疑问——一个系统的参与性越强,就越‘合法’。”
——抛弃数字乌托邦
但是,即使这样的制度能够完美地运作,我们想要保留中央集权的多数统治吗?仅仅是参与这一事实并不能使政治进程的强制性有所减弱。只要多数人有能力把自己的决定强加给少数人,我们谈论的就是一个在精神上与当今统治美国的制度相同的制度——这个制度还需要监狱、警察和税务员,或其他方式来履行同样的职能。
真正的自由不在于回答问题的过程有多参与,而在于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自己提出问题——以及我们能否阻止别人把他们的答案强加给我们。在独裁统治或民选政府下运作的机构,在没有代表调解的情况下,由多数人直接使用时,其压迫性并不会降低。归根结底,即使是最直接的民主国家也更善于集中权力,而不是最大化自由。
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民主是国家治理的一种手段。一些民主支持者试图改变话语,认为真正的民主只发生在国家之外,反对国家对权力的垄断。对于国家的反对者来说,这似乎是一个战略举措,因为它占用了三个世纪以来人民运动和沾沾自乐的国家宣传中投入在民主上的所有合法性。然而,这种方法存在三个基本问题。
“民主一开始就不是国家的一种形式。首先,人民权力的现实是永远不可能与国家的形式相吻合的。民主作为一种思考和行动的共同权力的行使,与国家之间总是存在紧张关系,而国家的原则就是占有这种权力……公民的权力首先是他们为自己采取行动的权力,是他们将自己构成一种自治力量的权力。公民身份不是一种与登记为一国居民和选民有关的特权;最重要的是,这是一项不能委托的工作。”
—雅克·朗西埃
首先,它与历史无关。民主起源于国家政府的一种形式;实际上,所有我们熟悉的民主历史例子都是通过国家或至少是由渴望治理国家的人来实现的。我们对民主的积极联想是后来才出现的一套抽象的愿望。
其次,它助长了混乱。那些提倡将民主作为国家的替代品的人很少在这两者之间做出有意义的区分。如果你放弃了代表、强制执行和法治,却保留了民主作为治理手段的所有其他特征——公民身份、投票和合法性在单一决策结构中的集中——你最终会保留政府的程序,而没有使其有效的机制。这结合了两种最坏的情况。它确保了那些接近反国家民主,期望它履行与国家民主相同功能的人将不可避免地失望,同时创造了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反国家民主倾向于在更小的范围内复制与国家民主相关的动态。
最后,这是一场必败之战。如果你想用民主这个词来表示的东西只能发生在国家框架之外,那么使用一个与国家政治联系了2500年的术语就会产生相当大的歧义。[7]大多数人会认为你所说的民主毕竟是可以与国家和解的。这为中央集权主义政党和策略在公众眼中重新获得合法性奠定了基础,即使在完全失去信誉之后也是如此。民主社会力量党(Podemos)和激进左翼联盟(Syriza)凭借直接民主的言论,在巴塞罗那和雅典被占领的广场上获得了支持,但最终却进入了政府大厅,在那里他们的行为与其他任何政党都一样。他们仍然在实行民主,只是更有效率。如果没有一种语言来区分他们在议会中所做的和人们在广场上所做的,这个过程将会一次又一次地重演。
“我们必须同时成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否则统治者和臣民的制度是唯一的选择……换句话说,自由只能通过分享政治权力来维持,而这种分享是通过政治机构来实现的。”
——辛迪·米尔斯坦,《民主是直接的》
当我们认识到我们反对国家时所做的事情是民主的实践时,我们就为我们的努力重新融入更大的代表性结构奠定了基础。民主不仅是管理政府机构的一种方式,也是使政府机构再生和合法化的一种方式。候选人、政党、政权,甚至是政府形式,当它们明显不能解决选民的问题时,都可以不时地更换。这样,政府本身——至少是其中一些问题的根源——就能够继续存在下去。直接民主只是重塑美国形象的最新方式。
即使没有我们熟悉的国家外衣,任何形式的政府都需要某种方式来决定谁可以参与决策,以及以什么条件参与决策——同样,谁可以算作民众。这些规定一开始可能含糊不清,但随着机构的发展和风险的增加,这些规定会变得越来越具体。如果没有强制执行决策的方法——没有kratos——政府的决策过程就不会比人们自主做出的决策更有分量。[8]这是一个寻求政府而非国家的项目的悖论。
这些矛盾在默里·布克钦(Murray Bookchin)将自由意志自治主义作为国家治理的替代方案的表述中足够明显。布克钦解释说,在自由意志自治主义中,一个由法律和宪法管理的排他性和公开的先锋组织将通过多数投票做出决定。他们将在市议会选举中推选候选人,长期目标是建立一个可以取代州政府的联邦。一旦这样一个联盟开始运作,即使参与的城市想要退出,其成员资格也将具有约束力。那些试图在没有国家的情况下保留政府的人很可能会以另一国家而告终。
因此,重要的区别不在于民主和国家之间,而在于政府和自决之间。政府是对特定空间或政体行使权力的过程:无论过程是独裁的还是参与的,最终结果都是施加控制。相比之下,自决意味着按照自己的方式发挥自己的潜力:当人们一起参与其中时,他们不是在统治对方,而是在培养累积的自主权。自由达成的协议不需要强制执行;将合法性集中在单一机构或决策过程中的制度总是如此。
用民主这个词来形容国家本质上是不受欢迎的,这很奇怪。这种想法的恰当说法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反对一切排斥和支配,支持权力结构、决策过程和合法性概念的彻底分散。这不是一个以完全参与的方式进行管理的问题,而是要使任何形式的统治都不可能强加于人。
共识与一致统治的幻想
如果民主政府的共同点是公民身份和治安——demos和kratos——那么最激进的民主会将这些类别扩大到包括整个世界:普遍公民身份,社区治安。在理想的民主社会中,每个人都是公民,[9]每个公民都是警察。[10]
在这一逻辑的最极端,多数决定原则意味着协商一致的统治:不是多数人的统治,而是一致的统治。我们越接近一致,政府就越被认为是合法的——那么,通过一致意见统治的政府难道不是最合法的政府吗?然后,最后,任何人都不需要扮演警察的角色。
“从严格意义上讲,真正的民主从来没有过,将来也永远不会有……人们很难想象全体人民会长期坐在一个议会中处理公共事务。”
——让-雅克·卢梭《社会契约论》
显然,这是不可能的。但值得反思的是,将直接民主理想化为一种政府形式意味着什么样的乌托邦。想象一下,要产生足够的凝聚力来通过共识过程来治理一个社会——让每个人都同意——需要什么样的极权主义。说到把事情简化到最小公分母!如果替代强制的办法是消除分歧,那么肯定还有第三条道路。
这个问题在占领运动中凸显出来。一些参与者将大会理解为运动的管理机构;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人们未经一致同意就采取行动是不民主的。另一些人则将集会视为没有规定权威的相遇空间,在那里人们可以交流影响力和想法,围绕共同的目标形成流动的星座,采取行动。前者在他们的占领者同伴采取大会未同意的策略时感到被背叛;后者反驳说,授予任意召集的群众否决权没有意义,其中包括任何在街上经过的人。
也许答案是,决策结构必须分散,并以共识为基础,这样就没有必要普遍达成一致。这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人们应该如何划分政治?什么规定了议会的管辖权或它可以做出的决定的范围?谁决定一个人可以参加哪些集会,或者谁受某个决定的影响最大?如何解决程序集之间的冲突?这些问题的答案要么是将一套管理合法性的规则制度化,要么是优先考虑自愿形式的结社。在前一种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规则可能会僵化,因为人们会参考协议来解决争议。在后一种情况下,决策结构将不断地转移、断裂、冲突,并在有机过程中重新出现,这很难被描述为政府。当决策过程的参与者可以自由地退出决策或从事与决策相矛盾的活动时,那么所发生的就不是政府,而是简单的对话。[11]
“民主意味着通过讨论来治理政府,但只有当你能阻止人们谈论时,它才有效。”
——克莱门特·艾德礼,英国首相,1957年
从一个角度看,这是一个重点问题。我们的目标是建立理想的制度,使它们尽可能地横向和参与,但把它们作为权威的最终基础吗?或者我们的目标是最大化自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创造的任何特定制度都是自由的附属,因此是可有可无的?再说一次,什么才是合法的,是制度还是我们的需求和欲望?
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制度也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它们本身没有任何价值。任何人都不应被迫遵守任何压制她的自由或未能满足她的需要的机构的规定。如果每个人都能在完全自愿的基础上自由地与其他人组织起来,这将是产生真正符合参与者利益的社会形式的最佳方式:因为一旦一种结构不能为所有参与者服务,他们就必须改进或取代它。这种方法不会使整个社会达成共识,但它是保证共识产生时具有意义和可取性的唯一方法。
被排斥者:种族、性别和民主
我们经常听到支持民主的论点,理由是民主是最具包容性的政府形式,最适合打击我们社会中的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然而,只要统治者/被统治者和被包容/被排斥的类别被纳入政治结构,被编码为“多数人”和“少数人”,即使少数人的数量超过多数人,沿着种族和性别界限的权力不平衡总是会反映为政治权力的差异。这就是为什么女性、黑人和其他群体仍然缺乏与其数量相称的政治影响力,尽管他们表面上拥有投票权已经有一个多世纪了。
“我们没有从美国的民主中获益。我们遭受的只是美国的虚伪。”
——马尔科姆·艾克斯,《选票还是子弹》
在《白人民主的废除》一书中,已故的乔尔·奥尔森对他所谓的“白人民主”提出了令人信服的批评——通过被授予白人特权的人之间的跨阶级联盟,将民主政治权力集中在白人手中。但他理所当然地认为,民主是最理想的制度,认为白人至上主义是民主运作的偶然障碍,而不是民主运作的自然结果。如果民主是平等主义关系的理想形式,为什么它在几乎整个存在期间都与结构性种族主义有牵连?
在政治被构建为零和竞争的地方,掌权的人将不愿与他人分享权力。想想那些反对普选的人和那些反对将投票权扩大到有色人种的白人:民主的结构并没有阻止他们的偏执,反而给了他们将其制度化的动力。
奥尔森追溯了统治阶级为了分化工人阶级而培育白人至上主义的方式,但他忽略了民主结构为这一过程提供的方式。他认为我们应该促进阶级团结来应对这些分歧,但是(正如巴枯宁反对马克思所主张的那样)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差异本身就是一种阶级差异——想想古雅典。种族排斥一直是公民身份的另一面。
“通过建立一个奴隶社会,美国为其伟大的民主实验创造了经济基础……美国不可或缺的工人阶级作为政治领域之外的财产存在,让美国白人可以自由地宣扬他们对自由和民主价值观的热爱。”
——塔-内希斯·科茨,《赔款案》
因此,白人至上主义的政治层面不仅仅是经济实力上的种族差异的结果——它也产生了这种差异。早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民族和种族分歧就在我们的社会中根深蒂固;宗教裁判所对犹太人财产的没收为美洲最初的殖民提供了资金,对美洲的掠夺和对非洲人的奴役为欧洲和后来的北美资本主义提供了最初的启动资金。种族分裂也有可能比下一次大规模的经济和政治转变持续得更久——例如,以白人(或犹太人,甚至库尔德人)公民为主的排他集会。
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改革者经常说要让我们的政治制度更加“民主”,他们的意思是更加包容和平等。然而,当他们的改革以一种使政府机构合法化和加强的方式实现时,这只会使这些机构在打击目标和边缘化群体时获得更多的支持——见证了自民权运动以来对黑人的大规模监禁。马尔科姆·艾克斯(Malcolm X)和其他黑人分离主义的倡导者认为,白人建立的民主永远不会给黑人带来自由,这是正确的——不是因为白人和黑人永远无法共存,而是因为在把政治变成对中央政治权力的竞争时,民主治理会产生冲突,使共存成为可能。如果今天的种族冲突能够得到解决,那将是通过在权力下放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关系,而不是通过将被排斥者纳入被包容者的政治秩序。[12]
“只要有警察,你觉得他们会骚扰谁?”只要还有监狱,你觉得谁能把它们填满?只要有贫穷,你认为谁会贫穷?相信我们可以在一个以等级制度为基础的社会中实现平等是天真的。你可以洗牌,但还是那副牌。”
——改变一切
只要我们理解我们在政治上共同做的事情是民主的——作为一个合法决策过程的政府——我们就会看到合法性被用来证明那些在功能上是白人至上主义的项目是合理的,无论是一个国家的政策还是发言人委员会的决定。(例如,回想一下以白人为主的全体大会与许多占领运动团体中白人较少的营地之间的决策过程之间的紧张关系。)只有当我们摒弃任何政治进程本质上都是合法的想法时,我们才能够消除一直是民主治理特征的种族差异的最后借口。
说到性别,这让我们有了一个新的视角,来理解为什么露西·帕森斯、艾玛·戈德曼和其他女性认为,要求女性投票权没有抓住重点。为什么有人会拒绝参与选举政治,尽管它并不完美?简而言之,她们想要彻底废除政府,而不是让政府更具参与性。但仔细观察,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更具体的原因,为什么关注妇女解放的人可能会怀疑这项公民权。
“人类政治活动的历史证明,政治活动所给予人类的一切,都是人类以更直接、更少代价和更持久的方式所不能达到的。事实上,他所取得的每一寸土地都是通过不断的斗争,通过为自我主张而不断的斗争,而不是通过选举权。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妇女在争取解放的过程中,已经或将会得到选举权的帮助。”
——艾玛·戈德曼,《妇女选举权》
让我们回到polis和oikos——城市和家庭。民主制度依赖于正式区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公共领域是所有合法决策的场所,而私人领域则被排除在外或打折扣。纵观许多社会和时代,这种划分已经被深刻地性别化了,男性主导着公共领域——所有权、有偿劳动、政府、管理和街角——而女性和那些性别二元之外的人则被贬到私人领域:家庭、厨房、家庭、养育孩子、性工作、护理工作,以及其他形式的无形和无偿劳动。
就民主制度将决策权和权威集中在公共领域而言,这就再现了父权的权力模式。这在妇女被正式排除在投票和政治之外时表现得最为明显,但即使她们没有被排除在外,她们在公共领域也经常面临非正式障碍,而在私人领域则承担着不成比例的责任。
将更多的参与者纳入公共领域有助于进一步使妇女和那些不符合性别规范的人处于不利地位的空间合法化。如果“民主化”意味着决策权从非正式和私人场所转向更公共的政治空间,其结果甚至可能削弱某些形式的女性权力。回想一下,20世纪70年代建立的基层妇女庇护所是如何通过国家资助实现专业化的,以至于到90年代,创办这些庇护所的女性根本不可能胜任其中的初级职位。
因此,我们不能把妇女正式参与公共领域的程度作为解放的指标。相反,我们可以解构公共和私人之间的性别差异,验证在关系、家庭、家庭、社区、社交网络和其他不被视为政治领域一部分的空间中发生的事情。这并不意味着将这些空间正式化,或将它们整合到所谓的中性政治实践(gender-neutral political practice)中,而是将多种决策方式合法化,承认社会中的多种权力场所。
有两种方式来应对男性在政治领域的统治。第一种是努力使正式的公共空间尽可能地方便和包容——例如,登记妇女投票,提供儿童保育,规定必须参与决策的人数,在讨论中允许谁发言的权重,甚至像罗贾瓦那样,建立仅由妇女组成的具有否决权的集会。这一战略寻求实现平等,但它仍然假定所有权力都应归属于公共领域。另一种办法是确定那些已经赋予没有从男性特权中受益的人权力的决策场所和做法,并赋予他们更大的影响力。这种方法借鉴了长期存在的女权主义传统,即优先考虑人们的生活和经验,而不是正式的结构和意识形态,认识到多样性的重要性,重视通常看不见的生活维度。
这两种方法可以相互吻合和补充,但前提是我们放弃所有合法性都应集中在一个单一的体制结构中的想法。
反对自治的理由
有人反对决策结构应该是自愿的而不是强制性的,应该是分散的而不是单一的。我们被告知,如果没有一个解决冲突的中心机制,社会就会陷入内战;没有一个中央权威,就不可能抵御集权侵略者;我们需要中央政府来处理压迫和不公。
事实上,权力集中既可能解决冲突,也可能引发冲突。当每个人都必须从国家结构中获得杠杆,以获得对自己生活状况的控制时,这必然会产生摩擦。在以色列/巴勒斯坦、印度/巴基斯坦和其他不同宗教和种族的人在相对和平的情况下自治共存的地方,殖民强加的在单一国家框架内争夺政治权力的必要性产生了长期的种族暴力。这种冲突在19世纪的美国政治中也很常见,想想早期华盛顿和巴尔的摩选举周围的帮派战争,或者为流血的堪萨斯而战。如果这些斗争在美国不再普遍,也不能证明这个国家已经解决了它所产生的所有冲突。
中央集权政府被吹捧为解决争端的一种方式,它只是巩固了权力,这样胜利者就可以通过武力来维持自己的地位。当中央集权结构崩溃时,就像南斯拉夫在20世纪90年代引入民主制度时所做的那样,后果可能是血腥的。最好的情况下,中央集权只能延缓冲突,就像债务积累利息一样。
但是去中心化的网络有机会对抗中心化的权力结构吗?如果他们不能,那么整个讨论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任何尝试去中心化的尝试都会被更中心化的竞争对手粉碎。
答案还有待观察,但今天的中央集权绝不能确信自己是刀枪不入的。早在2001年,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就提出,分散的网络,而不是集中的等级制度,将成为21世纪的权力玩家。在过去20年里,从所谓的反全球化运动到占领运动,再到库尔德人在罗贾瓦的自治实验,那些成功地为新的实验(包括民主和无政府主义)打开空间的举措都是分散的,而激进左翼联盟(Syriza)等更集中的努力几乎立即被吸收。目前,许多学者正在对基于网络的组织的特点和优势进行理论化研究。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即一个社会是否需要一个中央集权的政治机构来制止压迫和不公正。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在1861年南北战争前夕发表的第一次就职演说,是对这一论点最有力的表达之一。值得详细引用的是:
显然,分裂的核心思想是无政府状态的本质。被宪法的制约和限制所约束,并且随时随民意和情绪的有意变化而变化的多数派,是自由人民唯一真正的主权者。谁拒绝它,谁就必然走向无政府状态或专制。一致同意是不可能的。少数人的统治,作为一种永久的安排,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因此,拒绝多数原则,就只剩下某种形式的无政府主义或专制主义……
从物理上讲,我们不能分离。我们不能把我们各自的部分从彼此之间移开,也不能在它们之间建立一道不可逾越的墙。丈夫和妻子可以离婚,不再露面,彼此疏远,但我们国家的不同地区不能这样做。他们不得不面对面,他们之间必须继续交往,无论是友好的还是敌对的。那么,是否有可能使分离后的交往比以前更有利或更令人满意呢?外国人订立条约会比朋友订立法律容易吗?外国人之间的条约能比朋友之间的法律更忠实地执行吗?假设你去打仗,你不能一直打下去;当双方都损失惨重,而双方都无利可图之后,你们停止战斗时,关于交往条件的同样的老问题又会摆在你们面前。
这个国家,包括它的制度,属于居住在这个国家的人民。每当他们对现有政府感到厌倦时,他们就可以行使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来修改它,也可以行使革命赋予他们的权利来肢解或推翻它。
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里,按照这个逻辑走得足够远,你就会得到世界政府的概念:在整个星球的规模上由多数人统治。林肯是对的,反对达成共识的党派,一致的统治是不可能的,那些不希望被多数人统治的人必须在专制和无政府状态之间做出选择。他的论点是,外星人不能比朋友更容易订立条约制定法律,起初听起来很有说服力。但是朋友之间不会相互强制执行法律——法律是用来强加给弱小的一方的,而条约是在平等的一方之间订立的。政府不是朋友之间的事,正如一个自由的民族不需要君主一样。如果我们必须在专制、多数人统治和无政府状态之间做出选择,无政府状态是最接近自由的东西——林肯称之为我们推翻政府的“革命权利”。
然而,林肯将无政府状态与南方各州的分裂联系在一起,对自治提出了批评,这种批评至今仍在回响。这种观点认为,如果不是联邦政府,奴隶制就永远不会被废除,南方也不会废除种族隔离或赋予有色人种公民权利。这些反对不公正的措施必须在联邦军队和一个世纪后的国民警卫队的枪口下实施。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权力下放似乎意味着接受奴隶制、种族隔离和三k党。如果没有一个合法的中央管理机构,有什么机制可以阻止人们采取镇压行动呢?
这里有几个错误。第一个错误是显而易见的:在林肯的三个选择中——专制、多数人统治和无政府主义——分裂主义者代表的是专制,而不是无政府主义。同样,设想中央政府的机器将完全用于自由的一方是天真的。负责监督南方种族融合的国民警卫队使用实弹镇压了全国各地的黑人起义;今天,美国监狱里的黑人人数几乎和美国曾经的奴隶人数一样多。最后,人们不必为了反对压迫而把所有的合法性都赋予一个管理机构。一个人仍然可以采取行动——他必须不以执行法律为借口而这样做。
反对权力和合法性的集中并不意味着退回到无为主义。有些冲突是必然发生的;没有办法绕过它们。它们源于真正不可调和的分歧,强加虚假的统一只能延缓它们的发展。在他的就职演说中,林肯以国家的名义请求暂停废奴主义者和奴隶制支持者之间的冲突——这是一场不可避免和必要的冲突,由于几十年无法容忍的妥协,这场冲突已经被推迟了。与此同时,像纳特·特纳(Nat Turner)和约翰·布朗(John Brown)这样的废奴主义者能够在不需要中央政治权威的情况下采取果断行动——事实上,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做,只是因为他们不承认中央政治权威。如果不是像他们这样的自主行动所产生的压力,联邦政府永远不会干预南方;如果有更多的人采取主动,奴隶制就不会存在,内战也就没有必要了。
换句话说,问题不在于混乱太多,而在于混乱太少。迫使奴隶制问题出现的是自治行动,而不是民主审议。更重要的是,如果有更多的无政府主义支持者,而不是多数人统治,南方白人不可能在重建后重新获得南方的政治霸权。
还有一件轶事值得一提。在他发表就职演说一年后,林肯在一个由有色人种自由人组成的委员会上发表演讲,主张他们应该移民到像利比里亚那样的另一个殖民地,希望其他美国黑人也能效仿。关于获得解放的黑人和美国白人公民之间的关系,他认为,
我们两个种族还是分开比较好……我们的人民不愿意你们这些自由的有色人种和我们在一起,尽管这可能很残酷。
因此,在林肯的政治宇宙论中,白人公民的城邦不能分离,但一旦贵族的黑人奴隶不再占据他们的经济角色,他们就最好离开。这足以把事情戏剧化:国家是不可分割的,但被排除在外的人是可以抛弃的。如果内战后获得自由的奴隶移民到非洲,他们就会及时经历欧洲殖民的恐怖,仅在比属刚果就有1000万人死亡。解决这种灾难的正确方法不是将全世界整合成一个由多数人统治的单一共和国,而是与所有将人民分为多数人和少数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制度作斗争,无论这些制度有多么民主。
解放的民主障碍
除非发生战争或奇迹,任何一个政府的合法性总是在被侵蚀;它只会腐蚀。无论国家做出什么承诺,都无法弥补我们不得不放弃对生活的控制。每一个具体的不满都凸显了这个系统性问题,尽管我们很少见树见林。
这就是民主发挥作用的地方:又一次选举,又一届政府,又一次乐观与失望的循环。
“民主是确保政府合法性的好方法,即使它在提供公众想要的东西方面做得不好。在一个正常运作的民主国家,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会挑战统治者。他们没有挑战这个国家政治制度的根本性质。”
——诺亚·费尔德曼,《突尼斯这次的抗议活动有所不同》
但这并不总能安抚民众。在过去的十年里,世界各地都发生了运动和起义——从瓦哈卡到突尼斯,从伊斯坦布尔到里约热内卢,从基辅到香港——这些幻灭和不满的人试图把事情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人都团结在更多更好的民主的标准下,尽管这很难说是一致的。
考虑到市场和政府对我们施加的力量有多大,我们确实很容易想象我们可以以某种方式扭转局面并统治它们。即使是那些不相信人民有可能统治世界的人,通常也会以统治留给他们的一件事而告终——他们对统治的反抗。他们将抗议运动视为直接民主的实验,着手为一个更民主的世界的结构作预示。
但如果预示民主是问题的一部分呢?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这些运动中很少有人能够对他们所反对的结构发起不可调和的反对。除了恰帕斯(Chiapas)和罗贾瓦(Rojava)这两个有争议的例外,所有这些人都被击败了(占领运动),重新融入了现行政府的运作(激进左翼联盟(Syriza)、民主社会力量党(Podemos)),或者更糟的是,在没有实现任何真正的社会变革的情况下推翻并取代了政府(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乌克兰)。
当一场运动试图在与国家民主同样的原则基础上使自己合法化时,它最终会试图在自己的游戏中击败国家。即使它成功了,胜利的回报是被吸收和制度化——无论是在现有的政府结构内,还是通过重新改造它们。因此,以反抗国家而开始的运动最终会重新创造国家。
“偶尔你会反抗,但只是从头开始做同样的事情。”
——艾伯特·利伯塔德,《选民:你们才是真正的罪犯》
这可以以许多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有些运动声称自己比当局更民主、更透明或更具代表性,从而削弱了自己;通过选举政治上台的运动,却背叛了他们最初的目标;推动直接民主策略的运动被证明对那些寻求国家权力的人同样有用;还有推翻政府的运动,只是为了取代他们。让我们依次考虑这些问题。
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行动限制在大多数参与者事先都能同意的范围内,我们可能一开始就无法让他们离开地面。当大多数人已经接受了政府及其法律的合法性时,大多数人都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做任何可能挑战现有权力结构的事情,无论它对他们有多糟糕。因此,一个通过多数投票或共识做出决定的运动可能很难同意使用最具象征意义的策略。你能想象密苏里州弗格森市的居民召开共识会议,决定是否烧毁QuikTrip商店并击退警察吗?然而,正是这些行动引发了后来被称为“黑人的命也是命”的运动。人们通常要经历新事物才能接受它;把整个运动局限在大多数参与者已经熟悉的范围内是错误的。
出于同样的原因,如果我们坚持让我们的行动完全透明,那就意味着让当局来决定我们可以使用哪些策略。在广泛渗透和监视的情况下,以完全透明的方式公开进行所有决策,会使任何被视为对现状构成威胁的人受到压制。一个决策机构越是公开透明,它的行动就可能越保守,即使这与它存在的明确理由相矛盾——想想所有的环境联盟,它们从未采取过任何行动来阻止导致气候变化的活动。在民主逻辑中,要求政府透明度是有道理的,因为它应该代表人民并对人民负责。但在这种逻辑之外,我们不应该要求社会运动的参与者相互代表和回答问题,而是应该寻求最大限度地赋予他们行动的自主权。
如果我们以代表公众为理由宣称合法性,我们就为当局提供了一种轻易击败我们的方法,同时也为其他人利用我们的努力开辟了道路。在实行普选制之前,人们可以认为一场运动代表了人民的意愿;但如今,一场选举能吸引更多的人去投票,甚至超过最大规模的运动能动员到街头的人数。选举的获胜者总是能够声称自己代表的人数多于能够参与运动的人数。[13]同样,声称代表社会中最受压迫阶层的运动也可以被那些阶层的象征性代表纳入权力大厅所挫败。只要我们认可代表制的理念,一些新的政治家或政党就可以利用我们的言论来掌权。我们不应该声称我们代表人民——我们应该宣称没有人有权统治我们。
当一个运动通过选举政治上台时会发生什么?卢拉和他的工人党在巴西的胜利似乎呈现了一个最好的情况,一个基于基层激进组织的政党接管了国家。当时,巴西举办了一些世界上最强大的社会运动,包括150万人参加的土地改革运动MST(无地工人运动);其中许多都与工人党有关。然而,卢拉2002年上台后,社会运动进入了断崖式的衰退,一直持续到2013年。工人党成员退出了地方组织,在政府中担任职务,而现实政治的必要性阻止了卢拉对他以前支持的运动做出让步。MST迫使卢拉之前的保守政府将许多土地占领合法化,但在卢拉执政期间没有任何进展。这种模式在整个拉丁美洲反复出现,被认为是激进的政治家背叛了让他们上台的社会运动。如今,巴西最强大的社会运动是反对工人党(Workers’Party)的右翼抗议活动。通往自由没有选举捷径。
如果我们不寻求国家权力,而是专注于推广邻里会议等直接民主模式呢?不幸的是,这种做法可能被用来服务于各种各样的议程。2012年斯洛文尼亚起义后,在卢布尔雅那自发组织的社区集会继续举行的同时,一个由市政当局资助的非政府组织开始在一个“被忽视的”社区组织集会,作为“振兴”该地区的试点项目,明确意图吸引心怀不满的市民重新与政府对话。在2014年乌克兰革命期间,法西斯政党斯沃博达(Svoboda)和右翼党(Right Sector)通过在被占领的独立广场(Maidan)举行民主集会而崭露头角。2009年,希腊法西斯政党金色黎明党(Golden Dawn)成员与雅典Agios Panteleimonas社区的当地人一起组织了一次集会,协调对移民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攻击。如果我们要促进包容性和自决,仅仅宣传参与式民主的说辞和程序是不够的。[14]我们需要传播一个框架,反对国家和其他形式的等级权力本身。
即使是明确的革命战略也可以以民主的名义为世界大国的利益服务。从委内瑞拉到马其顿,我们看到国家行为体和既得利益者将真正的民众异见转化为虚假的社会运动,以缩短选举周期。通常,这样做的目的是迫使执政党辞职,以一个更“民主”的政府取而代之。英国政府更容易服从美国或欧盟的目标。这类运动通常聚焦于“腐败”,暗示只要正确的人掌权,这个体系就会运转良好。当我们走上街头时,与其冒着被某些外交政策所欺骗的风险,我们不应该动员起来反对任何特定的政府,而应该反对政府本身。
埃及革命戏剧性地说明了民主革命的死胡同。在数百人为推翻独裁者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并建立民主制度而牺牲后,普选让另一位独裁者穆罕默德•穆尔西(Mohamed Morsi)上台。一年后的2013年,一切都没有改善,发起革命的人们再次走上街头,拒绝民主的结果,迫使埃及军方废黜了穆尔西。今天,军方仍然是埃及事实上的统治者,曾经引发两次革命的压迫和不公仍在继续。军方、穆尔西和反抗的人民所代表的选择与林肯在就职演说中所描述的是一样的:暴政、多数人统治和无政府状态。
在这里,在反对贫穷和压迫的斗争的极限上,我们总是与国家本身作斗争。只要我们服从统治,国家就会根据需要在多数决定和专制之间来回切换——这是同一基本原则的两种表达。国家可以有多种形态;就像植物一样,它可以死亡,然后从根部重新生长。它可以采取君主政体或议会民主制、革命独裁或临时委员会的形式;当当局逃之夭去,军队哗变时,国家就会像病菌一样,在一个看似水平的大会上,由秩序和礼仪的拥护者携带。所有这些形式,无论多么民主,都可以再生成一个能够粉碎自由和自决的政权。
避免拉拢、操纵和机会主义的一个可靠方法是拒绝使任何形式的统治合法化。当人们通过灵活的、横向的、分散的结构直接解决他们的问题和满足他们的需求时,就没有腐败的领导人,没有僵化的正式结构,没有单一的过程可以劫持。废除权力集中,那些想要夺取权力的人就无法从社会上得到任何好处。一个无法治理的民族很可能不得不抵御潜在的暴君,但它永远不会用自己的力量来支持他们的统治。
向着自由:出发点
民主的经典辩护是,它是最糟糕的政府形式——除了所有其他形式。但如果问题出在政府本身,我们就得从头来过。
在没有政府的情况下重塑人类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两个世纪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只触及了皮毛。出于分析的目的,我们将总结一些可以指导我们超越民主的基本价值观,以及一些关于如何理解我们可以做什么而不是统治的一般性建议。大部分工作仍待完成。
“无政府主义代表的不是最激进的民主形式,而是一种完全不同的集体行动范式。”
——乌里·戈登,《无政府状态!》
横向,去中心化,自治,无政府
仔细一看,民主并没有达到最初吸引我们的价值观——平等主义、包容、自决。除了这些价值观,我们还必须添加横向、去中心化和自治作为它们不可或缺的对等物。
自20世纪后期以来,“横向”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从萨帕塔(Zapatista)起义开始,到反全球化运动和阿根廷的叛乱,无领导结构的思想甚至已经蔓延到商界。
但是,如果我们不希望陷入平等的暴政中,那么去中心化和横向化同样重要,在这种暴政中,每个人都必须能够就任何人都能够做的事情达成一致。权力下放不是所有机构都必须通过的单一程序,而是意味着多个决策地点和多种形式的合法性。这样,当权力在一个环境中分配不均时,就可以在其他地方得到平衡。分散化意味着保留差异——战略和意识形态的多样性是运动和社区的力量源泉,就像自然界的生物多样性一样。我们既不应以亲近感为借口把自己分成同质的群体,也不应把我们的政治降低到最低的公约数。
去中心化意味着自主——一种自主行动的能力。自治可以适用于任何规模的层面——一个人、一个社区、一场运动、整个地区。为了获得自由,你需要控制周围的环境和日常生活的细节;你越能自给自足,你的自主权就越有保障。这并不意味着独立满足你所有的需求;它也可能意味着一种相互依赖,让你可以利用你所依赖的人。任何一个机构都不能垄断资源或社会关系的获取。一个提倡自主的社会需要工程师所说的冗余: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广泛的选择和可能性。
如果我们希望促进自由,仅仅肯定自治是不够的。[15]一个民族国家或政党可以主张自治;民族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也可以。一个人或一个群体是自主的这一事实,并不能说明他们与他人培养的关系是平等主义的还是等级分明的,是包容的还是排外的。如果我们希望最大限度地为每个人争取自主权,而不是简单地为自己寻求自主权,我们就必须创造一种社会环境,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没有人能够积累凌驾于他人的制度权力。
我们必须创造无政府状态。
神秘的机构
机构的存在是为我们服务的,而不是相反。它们对我们的服从没有内在的要求。我们永远不应该给他们比我们自己的需求和欲望更合理的投资。当我们的愿望与他人的愿望发生冲突时,我们可以看看制度进程能否产生一个让所有人都满意的解决方案;但是,一旦我们赋予一个机构裁决我们的冲突或支配我们的决定的权利,我们就放弃了我们的自由。
这不是对特定组织模式的批评,也不是对“非正式”结构胜过“正式”结构的争论。相反,它要求我们把所有模型都当作暂时的——我们不断地重新评估和重新发明它们。托马斯·潘恩想把法律立为国王,卢梭把社会契约理论化,最近的资本主义狂热者都梦想着一个只基于契约的社会,我们反对说,当关系真正符合所有参与者的最佳利益时,就不需要法律或契约了。
同样地,这并不是主张单纯的个人主义,也不是主张将人际关系视为可有可无的,也不是主张只与有相同喜好的人组织在一起。在一个拥挤、相互依存的世界里,我们不能拒绝与他人共存或协调。问题很简单,我们绝不能试图将关系立法。
我们可以在持续的基础上评估机构,而不是遵循蓝图或协议:它们奖励合作还是竞争?他们是分配权力,还是制造权力瓶颈?他们是否为每个参与者提供了按自己意愿发挥潜力的机会,还是强加于人的外部要求?它们是在双方都同意的条件下促进冲突的解决,还是惩罚所有违反法律体系的人?
“他向我们表明,如果我们的良心和理性谴责法律和制度,我们就永远不应该让自己受到任何考虑的诱惑,承认它们的存在是正当的。他告诫我们不要在意是否有多数人反对我们的原则和观点,无论多数人的数量有多大;大多数人有时只是有组织的暴民。”
——奥古斯特·邦迪,关于约翰·布朗
创造会面的空间
为了取代正式的集中决策场所,我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会面空间,在那里人们可以敞开心扉,接受彼此的影响,并找到与他们有相同优先事项的人。相遇意味着相互转化:建立共同的参照点,共同的关注点。会面的空间不是一个被赋予权力为他人作出决定的代表机构,也不是一个采用多数决定原则或共识的管理机构。这是一个机会,让人们在自愿的基础上尝试以不同的方式行动。
2001年在魁北克市举行的反对美洲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 of Americas)峰会的示威活动之前,发言人委员会是一个典型的会面场所。这次会议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广泛的自治团体,以抗议北美自由贸易区。与会者没有试图作出具有约束力的决定,而是介绍了他们的小组为尽可能的互利而准备和协调的倡议。大部分决策都是在小组间的非正式讨论中做出的。通过这种方式,成千上万的人能够在不需要中央领导的情况下同步行动,也不会让警方对即将展开的广泛计划有太多的了解。如果发言人委员会采用一种旨在产生团结和集中的组织模式,参与者可能会花整个晚上毫无结果地争论目标、战略和允许哪些策略。
过去二十年的大多数社会运动都是混合模式,将会面空间与某种形式的民主并置。例如,在占领运动中,营地充当了开放式的会面空间,而大会在形式上是作为直接的民主决策机构来运作的。这些运动大多取得了最大的效果,因为它们促成的会面为自主行动打开了机会,而不是因为它们通过直接民主将群体活动集中起来。[16]如果我们把这次会面作为这些运动的驱动力,而不是通过民主程序塑造的原材料,它可能有助于我们优先考虑我们最擅长的事情。
无政府主义者对民主话语的矛盾感到沮丧,有时会退缩,只根据先前存在的亲和力来组织自己。然而,种族隔离滋生了停滞和暴躁。最好是根据我们的条件和需求来组织,这样我们就能接触到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条件的人。只有当我们把自己理解为动态集体中的节点,而不是拥有静态利益的离散实体时,我们才能理解人们在占领运动等经历过程中所经历的快速蜕变,以及如果我们敞开心扉,遭遇改变我们的巨大力量。
培养集体,保留差异
如果没有任何制度、合同或法律能够规定我们的决定,我们如何就我们对彼此的责任达成一致?
一些人建议区分“封闭”群体和“开放”群体,前者的参与者同意对彼此的行为负责,后者不需要达成共识。但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如何在两者之间划清界限?如果我们在一个封闭的群体中对同伴负责,直到我们选择离开为止,而且我们可以随时离开,这与参与一个开放的群体没有什么不同。与此同时,不管你喜不喜欢,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群体中,共享着一个无法逃避的空间:地球。因此,这不是区分我们必须相互负责的空间和我们可以自由行动的空间的问题。问题是如何在各个层级上同时培养责任感和自主性。
为此,我们开始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创造相互满足的集体——在这些空间中,人们相互认同,并有理由彼此做正确的事情。这些组织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从住房合作社、社区集会到国际网络。与此同时,我们认识到,我们将不得不根据对参与者有益的亲密和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地重新配置它们。当一个配置必须改变时,这并不一定是失败的标志:相反,它表明参与者没有争夺霸权。与其将群体决策视为追求一致,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分歧产生的空间,冲突发挥的空间,以及随着不同社会星座的汇聚和分化而发生的转变空间。分歧和分离可能和达成一致一样可取,前提是它们出于正确的原因;大规模组织的优势应该足以阻止人们无缘无故地分裂。
我们的制度应该帮助我们梳理差异,而不是压制或淹没它们。一些从罗贾瓦回来的证人报告说,当那里的议会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时,它就分裂成两个机构,把资源分给它们。如果这是真的,它提供了一种自愿联合的模式,这是对强求一致式的民主统一的巨大改进。
解决冲突
有时分成不同的小组并不足以解决冲突。为了摆脱中央集权的强制,我们必须想出解决冲突的新方法。反对国家的人之间的冲突是维护国家霸权的主要资产之一。[17]如果我们想要创造自由的空间,我们就不能分裂到无法保卫这些空间的地步,我们也不能以造成新的权力失衡的方式来解决冲突。
民主最基本的功能之一就是提供一种解决争端的方法。投票、法庭和警察都是为了决定冲突而不是解决冲突;法治有效地实施了赢家通吃的模式来解决分歧。通过集中力量,一个强大的国家能够迫使不和的各方暂停敌对行动,即使是在双方都无法接受的条件下。这使得它能够压制干扰其控制的冲突形式,如阶级斗争,同时培养破坏横向和自主抵抗的冲突形式,如帮派战争。如果不考虑国家结构挑起和加剧暴力的方式,我们无法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宗教和种族暴力。
当我们赋予机构固有的合法性时,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解决冲突的借口,而是依赖于国家的调解。它使我们有借口以武力结束争端,并把那些在结构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排除在外。我们不是主动直接解决问题,而是以争夺权力而告终。
如果我们不承认国家的权威,我们就没有这样的借口:我们必须找到双方都满意的解决办法,否则将承受持续冲突的后果。这促使我们认真对待各方的需要和看法,培养化解紧张局势的技能。没有必要让每个人都同意,但我们必须找到不同的方式,而不是产生等级制度、压迫和无意义的对抗。走上这条道路的第一步是取消国家提供的不解决冲突的激励措施。
不幸的是,许多曾经为人类社会服务的解决冲突的模式现在已不复存在,被古代雅典和罗马的法院系统强行取代。我们可以从变革正义的实验模型中看到我们将不得不发展的替代方案
拒绝被统治
想象一个水平和分散的社会可能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可以想象集体和集会的重叠网络,人们在其中组织起来满足他们的日常需求——食物、住所、医疗、工作、娱乐、讨论、陪伴。由于相互依存,它们有充分的理由友好地解决争端,但没有人能强迫其他任何人留在一种不健康或无法实现的安排中。为了应对威胁,他们将以更大的临时队形动员起来,利用与世界各地其他社区的联系。
事实上,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许多无国籍的社会都是这样的。今天。像这样的模型继续出现在土著、女权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传统的交汇处。
“多数人有权统治少数人这一原则,实际上把一切政府都解决为两群人之间的较量,即谁是主人,谁是奴隶;一场竞赛,无论多么血腥,在事物的本质上,永远不会最终结束,只要人类拒绝成为奴隶。”
—莱桑德·斯普纳《并非叛国》
这就把我们带回到了起点——今天的希腊雅典。在这个民主最初诞生的城市,成千上万的人现在打着无政府主义的旗帜,以横向的、分散的网络组织起来。取代了古雅典公民权的排他性,它们的结构广泛而开放;他们欢迎逃离叙利亚战争的移民,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自由实验要么成功,要么失败。他们寻求以集体团结承诺来加强权力的分散分配,以取代政府的强制机器。他们不是联合起来实施多数决定原则,而是合作防止统治本身的可能性。
这不是一种过时的生活方式,而是一个长期错误的结束。
从民主到自由
让我们回到起义的高潮。成千上万的人涌向街头,以新的形式找到彼此,这提供了一种陌生而令人兴奋的代理感。突然之间,一切都交织在一起:言语和行为,思想和感觉,个人故事和世界事件。确定性——我们终于有了家的感觉——不确定性——终于有了开阔的视野。在一起,我们发现自己有能力做我们从未想象过的事情。
这种时刻的美妙之处超越了任何政治制度。冲突和意外达成的共识一样重要。这不是民主的运作方式,而是自由的体验——让我们共同掌握自己的命运。没有一套程序可以使这种情况制度化。这是我们必须一次又一次地从习惯和历史的虎口中夺取的战利品。
下次机会之窗打开时,与其再一次重塑“真正的民主”,不如让我们的目标是自由,自由本身。
[1] “I am truly free only when all human beings, men and women, are equally free. The freedom of others, far from negating or limiting my freedom, is, on the contrary, its necessary premise and confirmation.” –Mikhail Bakunin
[2] This seeming paradox didn’t trouble the framers of the US Constitution because the minority whose rights they were chiefly concerned with protecting was the class of property owners—who already had plenty of leverage on state institutions. As James Madison said in 1787, “Our government ought to secure the permanent interests of the country against innovation. Landholders ought to have a share in the government, to support these invaluable interests, and to balance and check the other. They ought to be so constituted as to protect the minority of the opulent against the majority.”
[3] In this context, arguing that “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 constitutes a feminist rejection of the dichotomy between oikos and polis. But if this argument is understood to mean that the personal, too, should be subject to democratic decision-making, it only extends the logic of government into additional aspects of life. The real alternative is to affirm multiple sites of power, arguing that legitimacy should not be confined to any one space, so decisions made in the household are not subordinated to those made in the sites of formal politics.
[4] This is a fundamental paradox of democratic governments: established by a crime, they sanctify law—legitimizing a new ruling order as the fulfillment and continuation of a revolt.
[5] “Obedience to the law is true liberty,” reads one memorial to the soldiers who suppressed Shay’s Rebellion.
[6] Just as the “libertarian” capitalist suspects that the activities of even the most democratic government interfere with the pure functioning of the free market, the partisan of pure democracy can be sure that as long as there are economic inequalities, the wealthy will always wield disproportionate influence over even the most carefully constructed democratic process. Yet government and economy are inseparable. The market relies upon the state to enforce property rights, while at bottom, democracy is a means of transferring, amalgamating, and investing political power: it is a market for agency itself.
[7] The objection that the democracies that govern the world today aren’t realdemocracies is a variant of the classic “No true Scotsman” fallacy. If, upon investigation, it turns out that not a single existing democracy lives up to what you mean by the word, you might need a different expression for what you are trying to describe. This is like communists who, confronted with all the repressive communist regimes of the 20th century, protest that not a single one of them was properly communist. When an idea is so difficult to implement that millions of people equipped with a considerable portion of the resources of humanity and doing their best across a period of centuries can’t produce a single working model, it’s time to go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Give anarchists a tenth of the opportunities Marxists and democrats have had, and then we may speak about whether anarchy works!
[8] Without formal institutions, democratic organizations often enforce decisions by delegitimizing actions initiated outside their structures and encouraging the use of force against them. Hence the classic scene in which protest marshals attack demonstrators for doing something that wasn’t agreed upon in advance via a centralized democratic process.
[9] In theory, categories that are defined by exclusion, like citizenship, break down when we expand them to include the whole world. But if we wish to break them down, why not reject them outright, rather than promising to do so while further legitimizing them? When we use the word citizenship to describe something desirable, that can’t help but reinforce the legitimacy of that institution as it exists today.
[10] In fact, the English word “police” is derived from polis by way of the ancient Greek word for citizen.
[11] See Kant’s argument that a republic is “violence with freedom and law,” whereas anarchy is “freedom and law without violence”—so the law becomes a mere recommendation that cannot be enforced.
[12] This far, at least, we can agree with Booker T. Washington when he said, “The Reconstruction experiment in racial democracy failed because it began at the wrong end, emphasizing political means and civil rights acts rather than economic means and self-determination.”
[13] At the end of May 1968, the announcement of snap elections broke the wave of wildcat strikes and occupations that had swept across France; the spectacle of the majority of French citizens voting for President de Gaulle’s party was enough to dispel all hope of revolution. This illustrates how elections serve as a pageantry that represents citizens to each other as willing participants in the prevailing order.
[14] As economic crises intensify alongside widespread disillusionment with representational politics, we see governments offering more direct participation in decision-making to pacify the public. Just as the dictatorships in Greece, Spain, and Chile were forced to transition into democratic governments to neutralize protest movements, the state is opening up new roles for those who might otherwise lead the opposition to it. If we are directly responsible for making the political system work, we will blame ourselves when it fails—not the format itself. This explains the new experiments with “participatory” budgets from Pôrto Alegre to Poznań. In practice, the participants rarely have any leverage on town officials; at most, they can act as consultants, or vote on a measly 0.1% of city funds. The real purpose of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is to redirect popular attention from the failures of government to the project of making it more democratic.
[15] “Autonomy” is derived from the ancient Greek prefix auto-, self, and nomos, law—giving oneself one’s own law. This suggests an understanding of personal freedom in which one aspect of the self—say, the superego—permanently controls the others and dictates all behavior. Kant defined autonomy as self-legislation, in which the individual compels himself to comply with the universal laws of objective morality rather than acting according his desires. By contrast, an anarchist might counter that we owe our freedom to the spontaneous interplay of myriad forces within us, not to our capacity to force a single order upon ourselves. Which of those conceptions of freedom we embrace will have repercussions on everything from how we picture freedom on a planetary scale to how we understand the movements of subatomic particles.
[16] Many of the decisions that gave Occupy Oakland a greater impact than other Occupy encampments, including the refusal to negotiate with the city government and the militant reaction to the first eviction, were the result of autonomous initiatives, not consensus process. Meanwhile, some occupiers interpreted consensus process as a sort of decentralized legal framework in which any action undertaken by any participant in the occupation should require the consent of every other participant. As one participant recalls, “One of the first times the police tried to enter the camp at Occupy Oakland, they were immediately surrounded and shouted at by a group of about twenty people. Some other people weren’t happy about this. The most vocal of these pacifists placed himself in front of those confronting the police, crossed his forearms in the X that symbolizes strong disagreement in the sign language of consensus process, and said ‘You can’t do this! I block you!’ For him, consensus was a tool of horizontal control, giving everyone the right to suppress whichever of others’ actions they found disagreeable.”
[17] Witness the Mexican autodefensas who set out to defend themselves against the cartels that are functionally identical with the government in some parts of Mexico, only to end up in gang warfare against each oth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