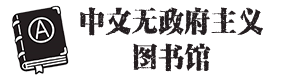Saul Newman
德里达对权威的解构
雅克·德里达思想的政治方面,特别是他对权威的批判,在某种程度上被忽视了。然而,他对哲学中理性和本质主义结构的质疑使得他的作品对任何当代政治制度和话语的批判,甚至对任何激进政治的理解都至关重要。德里达煽动了一系列的策略或“行动”,以揭露西方哲学话语中被压抑的对立和分歧,这些哲学话语的普遍性、整体性和清晰的自我反思自柏拉图时代以来就一直在发声。他的批评对政治理论有重要意义:他对哲学主张的质疑可以应用于以哲学为基础的政治制度的主张。德里达对本质和存在的形而上学结构及其可能产生的等级和统治之间的关系的讨论,以及他对对立和二元思维的批判,使他的作品被解读为对权力地位的攻击。在这里,权力地位指的是激进政治哲学和运动重申其试图推翻的权威结构的倾向。然而,解构主义的逻辑运作方式与福柯和德勒兹等思想家的后结构主义的扩散逻辑有所不同。德里达允许我们探索政治策略的可能性,它指的是一种激进的外在性,权力和权威的外在性。通过这个外在性,人们可以审问和抵制权威,而不用在权威的位置上调用另一种形式的权威。
解构主义
“解构主义”是最常与德里达联系在一起的术语,虽然它是一个被广泛误解和误用的术语,但它将在这里用来描述德里达工作的总体方向。克里斯托弗·诺里斯(Christopher Norris)将解构主义定义为一系列行动,其中包括拆除概念上的对立和思想的等级体系,以及揭示哲学中的“迷阵”(aporias)和自我矛盾的时刻。[1]可以说,解构主义是一种阅读文本——哲学文本——的方式,其目的是让这些文本质疑自己,迫使它们考虑自身的矛盾,暴露它们忽略或压抑的对立。然而,解构不是一个哲学体系。德里达不会站在另一种更完整、更不矛盾的体系的立场上,质疑一种哲学。我将指出,这只不过是用一种权威代替另一种权威。这是德里达竭力避免的陷阱。因此,他并非来自哲学之外的起点。系统之外没有必要的地方。相反,德里达在西方哲学本身的论述中工作,寻找隐藏的、危害西方哲学的对立。此外,他的目的并不是像人们经常宣称的那样破坏哲学。相反,德里达对哲学的批判本身就是哲学的。通过将哲学开放给这种质疑,德里达忠实于哲学的精神:毫无疑问和奴性的奉承最终成为对哲学的嘲弄。因此,解构主义是一种质疑哲学自反性自我认同的策略。
解构主义可以被视为对哲学中的权威结构的一种批判,特别是“逻辑中心主义”——也就是说,哲学在其整个历史中,从写作到话语的从属关系。哲学文本中话语高于写作的特权是德里达在西方哲学中所称的“存在形而上学”的一个例子。这表明哲学在多大程度上仍然植根于它声称已经超越的形而上学概念。德里达指出,在柏拉图的《费德鲁斯篇》中,写作被拒绝作为传达和记录真相的媒介:它被视为一种技巧,一种发明,不能代替与话语相关的意义的真实性和直接存在。当话语因其即时性而被视为接近真相的一种手段时,写作则被视为对言语话语的一种危险的腐蚀——一种较小的话语形式,它破坏记忆,容易被欺骗。此外,话语与教师的权威联系在一起,而写作被柏拉图视为对这种权威的威胁,因为它允许学生在没有教师指导的情况下学习。[2]
德里达通过指出其中的某些矛盾来攻击这种以逻辑为中心的思维。他指出,柏拉图除了通过写作的隐喻外,不能代表话语,同时又否认写作作为媒介有任何真正的功效。就像德里达说的:"在这里,所谓的生活话语应该突然被一个隐喻所描述,这个隐喻来自于一个人试图从它中排除的事物的秩序"[3]因此,话语依赖于它所排除的文字。写作是“补充逻辑”的一个例子:一个补充被存在所排除,但同时,它对其身份的形成是必要的。因此,写作是话语的补充:它被话语排除在外,但仍然是话语存在的必要条件。这种互补性逻辑的揭示是德里达抵制哲学上的逻辑中心主义的解构行动之一。话语声称是一种自我存在,对自己来说是直接和真实的,而写作被认为是在减少这种存在。然而,德里达表明,这种真实性,这种纯粹的自我认同总是值得怀疑的:它总是被它试图排除的东西所污染。根据这种逻辑,没有任何同一性是完整或纯粹的:它是由威胁它的事物构成的。德里达并不想否认自我认同或存在:他只是想表明,这种存在从来不像它声称的那样纯粹。它总是对一个事物敞开,却又被它所污染。
这种补充的逻辑可以应用于以本质同一性为中心的古典革命政治问题。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中,无产阶级是一个革命阶级,其身份在本质上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的。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这些结构实际上是无产阶级身份本身的补充,就像写作是讲话的补充一样?如果某种程度上,抵抗运动是由它声称要反对的势力构成的,那么任何抵抗运动的身份都是很有问题的。德里达的批评质疑了本质认同的问题,以及它是否能继续成为反对权力和权威的政治行动的基础。此外,他对自我认同的批判迫使我们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权力本身无法包含在稳定的身份中——比如国家。相反,权力是一种身份,它总是不稳定、偶然和分散的。
德里达继续了这种对本质身份的批判,不仅表明其统一和纯粹是可疑的,而且它构成了一个权威的身份。它在哲学上建立了一系列层次二元关系,一个术语从属于另一个术语。德里达将这些视为“暴力的等级制度”。语意中心主义建立了“说”与“写”的二元层次,即“写”隶属于“说”,“表示”隶属于“在场”。存在构成了一种文本权威形式,试图支配和排除其补充。然而,这种权威不断受到排除性补充的损害,因为它对形成主导术语的特性至关重要。然而,这些二元结构在哲学话语中形成了一个权力地位。它们为政治统治提供了基础。例如,福柯认为哲学对理性/非理性的二元分离是控制和监禁疯子的基础。哲学中的二元结构使支配的实践和话语永久化。
倒置/颠覆
然而,必须明确的是,德里达并不是简单地想要颠倒这些二元的术语,从而使从属术语成为特权术语。例如,他不想把写作放在说话的位置。这种方式的倒置保留了二分法的等级、权威结构。这样的战略只会在推翻它的企图中巩固权力的地位。有人可能会说,马克思主义是这种逻辑的牺牲品,因为它用同样专制的工人国家取代了资产阶级国家。这是一个萦绕在我们激进的政治想象中的逻辑。革命的政治理论往往只能成功地以自己的形象重塑权力和权威。然而,德里达也认识到颠覆的危险——也就是说,彻底推翻等级制度的激进策略,而不是推翻它的条款。例如,古典无政府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沿着马克思主义忽视政治权力-特别是国家权力-经济权力的路线,这将意味着在马克思主义革命中恢复政治权力。相反,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国家和一切形式的政治权力必须作为第一个革命行动被废除。然而,德里达认为,颠覆和倒置都以同一件事达到顶峰——以不同的伪装重塑权威。因此,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是基于权力所否认的人类理性和道德本质的启蒙思想,然而我们从德里达知道,任何本质的身份都涉及对其他身份的激进排斥或压制。因此,无政府主义取代了建立在启蒙人文主体性基础上的理性权威——政治权威和经济权威。因此,激进的政治理论策略——以马克思主义为例的倒置策略和以无政府主义为例的颠覆策略——都是同一个“地位”逻辑的两个方面。所以对德里达来说:
因此,必须发生的不仅是对所有等级制度的镇压,因为无政府状态只会同样肯定地巩固形而上学等级制度的既定秩序;它也不是任何给定等级制度的简单改变或逆转。相反,“乌姆德里洪”(Umdrehung)必须是等级结构本身的一种转变。[4]
换句话说,为了避免权威的诱惑,一个人必须超越破坏等级制度的无政府主义欲望,以及仅仅颠倒术语。相反,正如德里达所建议的,如果一个人想要避免这个陷阱,等级结构本身就必须改变。政治行动必须唤起对革命和权威的重新思考,在这两个词之间找到一条路径,这样它就不仅仅是重塑权力的地位。可以认为,德里达提出了他自己的无政府主义,如果无政府主义意味着对所有权威的质疑,包括文本和哲学权威,以及希望避免在试图摧毁权威和等级制度时重现权威和等级制度的陷阱。
这种解构主义试图改变等级和权威的结构,超越二元对立,这也在尼采身上发现。尼采认为,一个人不能仅仅通过肯定权威的对立面来反对权威:这只是对,因此,肯定一个人理应抵抗的统治作出反应。他认为,一个人必须完全超越对立思维——超越真理与错误,超越存在与生成,超越善与恶。[5]对尼采来说,这只是一种道德偏见,将真理置于错误之上。然而,他并没有试图通过将错误置于真理之上的特权来反击这一点,因为这让反对派毫发无损。相反,他拒绝将自己的世界观局限于这一对立:“事实上,是什么迫使我们假定在‘真’和‘假’之间存在任何本质上的对立?仅仅设想外表的明显程度,以及浅色和深色的色调,难道还不够吗?”[6]尼采取代,而不是替代,这些对立和权威的思想结构——他取代了地位。德里达同样采用的这种置换策略,为发展一种非本质主义的抵抗权力和权威的理论提供了一定的线索。人们或许应该质疑,并试图让二元对立的结构产生问题,而不是逆转这种对立的条件。
人之死
德里达认为,这些二元结构的流行表明,哲学在多大程度上仍然与形而上学联系在一起:,它仍然被形而上学的地位所支配。同样地,有人可能会说,政治理论仍然被一种需要所支配,它需要某种它从未拥有过的本质,而且还在不断地尝试革新。根据德里达的说法,政治和哲学对自我相同本质的要求,是神圣范畴的残余。上帝并没有完全从哲学中被篡夺,就像人们一直声称的那样。上帝只是以本质的形式被重新创造了。德里达在此受到尼采的影响,尼采认为,只要我们继续绝对相信语法,本质上,相信语言的形而上学预设,我们就继续相信上帝。尽管我们可能会说相反的话,但我们并没有把上帝从哲学中驱逐出去。这个地方,神圣范畴的权威仍然完好无损,只是被重新刻上了存在的要求。对德里达来说,人文主义论述的人已经取代了上帝:
这样命名的东西,无非是人与神在形而上学上的统一,人与神的关系,作为构成人类现实的计划而成为神的计划。无神论并没有改变这个基本结构。[7]
这个神-人的幽灵还没有从我们中间驱除。例如,德里达指出,海德格尔关于存在的概念并没有象它所宣称的那样取代神-人-本质的范畴,相反,存在只是重申了这一范畴。“存在”的概念只是人文本质的再创造,正如人只是上帝的再创造一样。宗教和形而上学的权威和地位仍然完好无损。[8]德里达的分析很重要,因为它揭示了威权主义仍然存在于某些思想结构中。此外,它表明,任何一种激进的政治理论必须首先意识到自己潜在的形而上学结构,从而意识到自己的统治潜力。
德里达认为,有必要思考人类的死亡,而不思考本质。换句话说,人们必须设法以一种避免危险的地位陷阱的方式来处理人类死亡的问题。哲学对人类死亡的宣告并没有完全说服德里达。因此,也许福柯敲响人类的丧钟——他预言人类的形象会像画在海边沙滩上的脸一样消失——我们应该持怀疑态度。[9]至少对德里达来说,仍然存在着不妥协的神-本质的幽灵,它拒绝被驱除:它仍然牢固地扎根于哲学中,甚至在政治中,一如既往。[10]此外,正如德里达所言,摧毁这个地位是不可能的。海德格尔通过预设一个前本体论的存在来克服形而上学,只是更加忠实于形而上学的传统。[11]这种绝对拒绝的策略,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永远不会奏效:它只是以另一种形式重塑权威。它构建了权威-权力/革命这一可疑的二元关系,在这一二元关系中,革命可能成为新的权力形式。
然而,福柯、德勒兹等后结构主义者是否也陷入了同样的陷阱?可以说,福柯将主体分散到权力和话语场所,德勒兹和瓜塔里将主体分裂成一种无政府的、随意的机器、部件和流动的语言,这些操作否定了激进政治的一个必要出发点。因此,在他们对人文主义的拒绝中,也许福柯,德勒兹和瓜塔里,自相矛盾地否认了他们反抗支配的可能性,他们认为支配不可避免地涉及人文主义话语。从这个意义上说,后结构主义给激进政治留下了理论空白。德里达在这里指出了后结构主义论证的局限性。
超越后结构主义
德里达让我们重新审视人文主义问题。他描述了在哲学中处理位置问题的两种可能的方式——解构主义的两种诱惑。第一个策略是:
试图在不改变领域的情况下,通过重复创始概念和原始问题中隐含的东西,通过使用房屋中可用的工具或石头来对抗建筑,也就是说,同样地,在语言中在这里,一个人有不断确认、巩固、提升(再提升)的风险,在一种更确定的深度,也就是人们所谓的解构。。持续的明确表达,走向开放的过程,有陷入封闭的自闭症的风险。[12]
所以这种在启蒙运动人文主义形而上学的话语中工作的策略,使用它的术语和语言,可能会重申和巩固结构,巩固权力的地位,这是人们试图反对的。德里达在这里谈论的是海德格尔对人文主义的批判,他认为,这涉及到用同样本质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存在取代人。
德里达认为,第二种策略是:
以一种不连续的、突兀的方式决定改变领域,把自己残酷地置于外部,并确定绝对的打破或不同。不用提其他所有的错视法,也可以看出这种位移,因此,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天真、更严格地居住在内部,宣称自己已被遗弃,语言的简单实践不断地在最古老的土地上恢复新的领域。[13]
这种与人文主义形而上学话语的绝对决绝,寻求一个可以逃避的外部,并从外部抵抗权威的替代行动,将代表后结构主义的逻辑。[14]例如,Alan Schrift在福柯的《词与物》中看到了这种策略。[15]正如我之前所说的,福柯和德勒兹可能被视为与人文主义的绝对断裂——将主体分散成话语、机器、欲望和实践等的碎片和效果。德里达认为,这与第一种策略的效果相同:试图完全改变领域,只会再次确认自己在旧领域中的位置。一个人越试图逃离主导范式,就越会在其中沮丧地发现自己。这是因为,在后结构主义在其对人本主义和主体的过于仓促的拒绝中,否定了自己对理性等本质主义人本主义话语的理论抵抗的出发点。德里达认为解构——就此而言,任何形式的对权威的反抗——总是夹在这两种可能策略的“锡拉”和“卡律布狄斯”之间,因此必须在它们之间航行。这两种解构策略将政治理论串了起来:它们是对抗反专制思想和反专制行动的两种可能路径。它们都受到地位的威胁。
德里达或许可以为我们指明一条走出理论深渊的道路。也许有一种方法可以将这两条看似不可调和的道路结合在一起,在某种程度上允许激进政治超越形而上学和人文主义的问题,而不重申这些结构。德里达认为,我们必须同时遵循两条道路,而不是选择一种战略而抛弃另一种。[16]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结合或编织这两种可能的行动,从而超越它们。例如,正如Alan Schrift所说,德里达并没有放弃主体的范畴——相反,他试图取代并重新评估它。[17]德里达不像福柯那样,以人的终结来思考问题,而是在形而上学中提到了人的“终结”。[18]不同的是,对德里达来说,人不会被完全超越,而是被重新评价,也许是按照尼采的超人。[19]对德里达来说,人的权威将在语言中被分散,但这个主题不会被完全抛弃。德里达拒绝抛弃主体的观点指向了政治思想的一些有趣的可能性:也许主体的范畴可以被保留为一个去中心化的、非本质主义的范畴,作为它自己的限制而存在,从而为政治提供了一个出发点。像福柯和德勒兹这样的思想家如此匆忙地抛弃“人”,可能忽略了“人”以另一种形式重新出现的可能性。所以德里达的批判是在这个问题的极限上进行的,从而指出了超越后结构主义论证的可能性。例如,他认为差异的母题是不充分的——虽然它声称避开本质,但也许它只允许另一个本质在它的位置上形成。
延异
解构主义试图解释哲学话语中被压抑、隐藏的差异和异质性:那是不统一和对立的低沉、半压抑的低语。德里达称这种策略为“延异”(differance)——用a来拼写差异,以表示它不是绝对的、本质的差异。它毋宁是差异或差异的运动,差异作为差异的身份始终是不稳定的,从来不是绝对的。正如德里达所说:“延异是我们可能给“积极的”,不同力量的移动的不和,以及力量的差异的名称……反对整个形而上学语法体系。”[20]因为延异并不构成差异的本质同一性,因为它对偶然性开放,从而破坏固定的同一性,它可能被视为反专制政治的工具:“它不统治任何东西,统治任何东西,没有任何地方行使任何权威……不仅没有延异的王国,而且延异会煽动对每一个王国的颠覆。”[21]
这一系列的差异有一个结构,或者如Rodolphe Gasché所说,一个“基础结构”。[22]基础结构是一种交织,是差异和对立的无序组合。此外,这是一个系统,它的本质是一种非系统的性质:构成它的差异并没有被基础所分解,也没有被安排到一个辩证的框架中,在这个框架中,它们的差异只成为对立的二元关系。[23]这是一个非辩证、非二元差异的“系统”:它以一种既不排序也不抹去它们的方式将差异和对立串联在一起。基础结构不是本质主义:它们的本质是一种非本质。[24]它没有一个稳定的或自治的身份,也不受一个秩序原则或权威的支配。它是一个回避本质、权威和中心的“地方”:它的特点是无法构成一个身份,无法形成一个地方。此外,它在结构上无法建立稳定的身份,这对身份的权威性构成了威胁。就像德里达说的:
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它不仅不能允许人们把它自己当作它的名称或它的表象的本身来看待,而且它威胁到一般的事物本身的权威,即事物在其本质上的存在。[25]
也正是在这里,德里达超越了后结构主义的论点。虽然他采用了一种差异模型,就像福柯和德勒兹一样,但他用的方式略有不同:延异指的是某种结构或基础结构,某种建立在自身不统一基础上的统一,并通过自身的限制构成。因为后结构主义缺乏这种基础结构在结构上保持开放的想法——即使对相同的可能性——它可以被视为差异的本质。所以矛盾的是,也许正是因为后结构主义缺乏一个结构或位置,就像德里达提供的那样,它落回到了一个位置——一个由本质主义思想构成的位置。德里达的论证指向了某种起点的需要——不是基于本质的同一性——而是通过补充的逻辑构建的,基于自身的污染。
基础结构可以被视为反专制思想的工具:它是一个模型,通过其自身结构上的位置缺失,通过其自身本质的缺失,从不同的文本权威结构内部破坏。它的核心是缺失。它受到不可判定原则的“支配”:它既不确定同一性,也不确定非同一性,但仍然处于两者之间不可判定的状态。基础结构是一种将差异理论化的方式,使得在哲学中形成稳定的、统一的身份是不可能的。它也是一种模式,允许思维超越限制它的二元结构。所以这个策略的目的不是要破坏身份或存在感。它不是肯定差异胜于认同,缺席胜于存在。正如我所建议的那样,这将是推翻现有的秩序,只是为了建立一种新的秩序。差异将成为一种新的身份,而缺失将成为一种新的存在。德里达思考的重点不是寻求建立一个新的秩序,而是寻求取代所有的秩序——包括他自己的秩序。
德里达认为,解构的策略不能完全在逻辑中心哲学的结构内起作用;它也不可能完全在外部运作。相反,它在两种立场之间追溯了一条不可判定的路径。解构主义以这种方式避免了位置的陷阱。它既没有建立一个权力的位置,也没有建立一个革命的位置——正如我所说的,这是同一统治逻辑的两个方面——而是在它们之间建立了一条道路,破坏了这两个术语的身份。它从哲学的话语和形而上学的结构中工作,在其限度内运作,以找到一个外部。[26]解构主义不能试图立即中和哲学的权威结构。相反,它必须通过一种置换的策略——德里达称之为“双重写作”,这是一种批判形式,既不是严格地在哲学内部,也不是严格地在哲学外部。这是一种不断质问这种自我宣告的话语结束(closure)的策略。它的做法是迫使政府对过剩的资源加以解释,从而危及这种结束。在德里达看来,这种越界行为无处可逃:它不构成反抗之地,一旦逃脱,它就解体了。这种越界正是由它所威胁的结构产生的:它是主导结构的补充,是必要的,但同时也是危险和任性的一部分。这种解构主义试图识别的过剩,与哲学的无限和封闭的限制相对峙。哲学所宣称的全面性和无限性本身就是一种限度。然而,它对威胁它的东西完全关闭是不可能的,因为正如解构主义所表明的,它试图排除的东西对它的身份是必不可少的。这里有一个奇怪的逻辑在起作用,这个逻辑不断地阻碍哲学成为一个封闭的、完整的系统的愿望。解构揭示了这个逻辑,这个极限的极限。
德里达所确定的限制是在哲学传统中产生的,它们不是来自虚无主义的,非理性的外部强加的。正如德里达所说:“解构主义的运动并不是从外部破坏结构。他们既不可能也不有效,也无法准确瞄准目标,除非他们居住在那些建筑里。”[27]这种界限的定位在这里很重要,因为它指出了外部的可能性——矛盾的是,外部是在内部。将自己完全置于任何结构的外部,作为一种反抗的形式,只是以一种相反的方式重申,你所反抗的是什么。然而,这种由内在的局限所创造的外在的观念,可能使我们构想出一种无法恢复权力地位的抵抗政治。所以德里达不仅提出了一种不退回到本质主义的理论差异的方法,他还指出了外部的可能性。
伦理责任的“外部”
因此,这种限制,这种封闭的不可能,或许同时,构成了一种可能的外部——一种由内部的限制和矛盾构成的外部。这些矛盾使其不可能结束;他们向他者开放哲学话语。这是一个激进的外部。它不是内/外二元结构的一部分,它没有一个稳定的身份。它并没有被一条不可阻挡的路线从内部明显地分割开来:它的“路线”不断地被对立的关系重新解释、破坏和建构。它是有限和暂时的外在。此外,它是一种服从一种奇怪逻辑的外在:它只存在于它所威胁的内在,而内在也只存在于它所威胁的内在。每一种都是构成另一种身份的必要条件,同时又威胁着另一种身份。因此,它是一种外在,避免了解构主义的两种诱惑:一方面,它是一种外在,威胁着内在;另一方面,它是由内部形成的外部。德里达明确指出,它不能被视为绝对的外部,因为这只会重新巩固它所反对的内部。一个人越是试图逃避到绝对的外在,就越是发现自己固执地停留在“内在”。正如德里达所说:“每一种与外部关系的“逻辑”都是非常复杂和令人惊讶的。正是这个系统的力量和效率经常把违规行为变成“错误的出口”[28]
对于德里达来说,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绝对决裂、绝对越界的概念,这是古典革命政治的核心,只是对人们希望逃离的“制度”的重申。德里达认为,越界只能是有限的,它不能建立一个永恒的外部:
…由于对界限的这一面和那一面所作的工作,就改变了里面的领域,从而产生了一种越界,因而这种越界在任何地方都不是既成事实。一个人永远不会安于罪恶之中,永远不会生活在别的地方。[29]
因此,解构主义可以被视为一种越界,在超越形而上学的极限的同时,也超越了它自己。[30]它不肯定任何东西,它不是来自于对立的外部,它一越过这个界限就消散了。它通过追踪文本中被压抑的缺失和不连续——文本没有包含的多余部分——来暴露文本的局限性。[31]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越界的。然而,它也是一种谦逊的运动——一种自我抵消的越界。解构主义既不肯定也不摧毁它“跨越”的界限:而是重新评估它,把它重新定义为一个问题(problem),一个问题(question)。这种越界界限的不确定性,这种不可判定性,是德里达最接近外界的东西。
对德里达来说,这种激进的外在是合乎伦理的。哲学对它所排斥的事物和它的对方敞开了大门。迫使哲学直面其自身的排斥和压抑结构的行为,是一种彻底的伦理姿态。德里达在这里受到了伊曼纽尔·列维纳斯的影响,列维纳斯试图思考黑格尔传统的局限性,通过展示它遇到了一个伦理外部的暴力,一个具有排他性和独特性的另类。列维纳斯试图超越西方哲学,通过与大他者对抗来破坏它,大他者是不适合其结构的不可还原点。[32]因此,解构可以被视为一种向他人开放哲学的伦理策略。它试图超越理性和历史必然性的界限,哪怕只是一瞬间,而这种“超越”,这种瞬间的越界,构成了一种伦理维度——一种另类伦理。德里达写道:
因此,要“解构”哲学,就要以一种最忠实的、内在的方式,去思考哲学概念的结构化谱系,但同时,要从哲学无法限定或无法命名的某种外在,去确定这段历史能够掩盖或禁止什么,并通过某种某种动机的压抑,使自己成为一段历史。[33]
这种对哲学的质疑并不会导致道德虚无主义,而解构主义常常被指责促进了这种虚无主义。正如约翰·卡普托(John Caputo)所言,解构是一种对被排斥者负责的策略。不同于诠释学试图将差异同化为相同的存在秩序,解构主义试图为差异打开空间。因此,德里达的思想是一种负责任的无政府状态,而不是一些人所说的不负责任的无政府状态。[34]因此,解构绝不是对伦理的拒绝,即使它质疑道德哲学:相反,它是对伦理的重新评价。[35]它向我们表明,道德原则不可能是绝对的或纯粹的:它们总是被它们试图排除的东西所污染。善总是被恶所污染,理性总是被非理性所污染。德里达所质疑的是道德的伦理:如果道德成为一种绝对的话语,那么它还能被认为是道德的或伦理的吗?解构让我们打开伦理的领域,重新解释和差异,而这种开放本身就是伦理的。这是一种不洁的伦理。如果道德总是被它的对方所污染——如果它从来就不是纯粹的——那么每一个道德判断或决定都必然是不可判定的。道德判断必须始终自我反省和谨慎,因为它的基础不是绝对的。与许多以人类本质的坚实基础为基础的道德哲学不同,解构主义伦理学没有这样的特权地位,因此也没有这样的自信。
法律、正义和权威
判断的不可判定性,是解构主义批判的必然结果,对政治话语和制度,尤其是法律制度,具有启示意义。德里达认为法律的权威是可疑的,在某种程度上是非法的。这是因为,作为法律依据的权威只有在法律制定时才被合法化。这意味着法律所建立的权威,严格地说,是不合法的,因为它必须先于法律存在。因此,最初制定法律的行为是一种不正当性,一种暴力:“因为权威的起源、基础或基础、法律的地位,从定义上讲,除了它们本身之外,不能建立在其他任何东西上,它们本身就是一种没有根据的暴力。”[36]像福柯一样,德里达表明法律和制度的起源是暴力的——它们是对立的,没有必要的基础。这并不意味着法律的起源是非法的:因为它们先于法律,所以它们既不合法也不非法。[37]相反,法律的合法性是不可判定的。对法律的解构式讯问揭示了法律大厦底部的缺失、空洞,以及机构权威根源上的暴力。因此,法律的权威可能受到质疑:它永远不能绝对统治,因为它被自己的根本暴力所污染。这种批判允许人们质疑任何声称基于法律权威的制度和政治话语,这使得它成为激进的反威权政治的宝贵工具。
然而,正如德里达所言,解构主义不能以彻底摧毁所有权威为目标:正如我们所见,这只会屈服于地位的逻辑。正如德里达所说,解构主义的两种诱惑可以被比作沃尔特·本雅明关于大罢工备选路径的概念——取代国家或废除它:
因为在每一种阅读中都有一种总罢工,因而也就有一种革命形势,它发现了一些新的东西,而这些新东西就现有的阅读准则和标准来说,仍然是不可读的,也就是说,现在的阅读状态,或者说,用大写字母S来表示国家处于可能阅读的状态。[38]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解构可以被视为一种对抗哲学文本中意义权威——国家的策略,就像其他斗争可能会在政治的“文本”中对抗国家一样。事实上,将哲学文本的解构与权力的解构分开是没有意义的:这两个斗争领域是不可分割的,因为政治权威依赖于各种文本的认可,比如霍布斯的那些,以及理性的逻辑中心话语。在这个意义上,解构的时刻是一个“革命性”的时刻。
然而,如果要避免在与法律的斗争中重建法律的权威,那么就必须将法律与正义区分开来。在德里达看来,法律只是一项规则的普遍适用,而正义则是法律对另一种规则的开放,对法律无法解释的奇点的开放。正义存在于与法律的一种他性关系中:它将法律的话语向外界开放。它解构地取代了法律。要使一个决定是公正的,要使它解释法律所否认的奇点,它必须每次都是不同的。它不能仅仅是规则的应用——它必须不断地重塑规则。因此,正义维护法律,因为它是以法律的名义运作的;但与此同时,它悬置了法律,因为它被不断地重新解释。正如德里达所说:“一个决定要公正负责,它必须……既要有监管,也要没有监管:它必须保存法律,也必须摧毁法律,或者悬置法律,以至于在每一种情况下都必须重新发明它,重新证明它的合理性。”[39]
此外,正义存在于一个伦理领域,因为它意味着行动的自由和责任。[40]正义是不可能的经验,因为它总是存在于一种悬置和不可判定的状态。它永远是不可估量的,是对未来的承诺,永远不能完全把握或理解,因为一旦把握或理解了,它就不再是正义,而成为法律。就像德里达说的,正义是存在的也是不存在的,除非某些事件是可能的,作为一个事件,超过了计算,规则,程序,预期。“[41]正义是一件向另一件事,向不可能的事敞开自己的大门。它的效果总是不可预测的,因为它不能像法律那样由先验的论述来决定。这是一种从法律中溢出的过剩,它不能被法律所掌握。正义作为一个开放的、空的能指:它的意义或内容不是预先确定的。德里达关于正义的概念没有预先确定的逻辑,这种正义的结构是由一种缺失,一种空虚所支配的,这使得它可以被重新解释和争论。
解放的政治
正义所占据的政治伦理维度不能被简化为法律或制度,正因如此,正义为法律和政治的转型打开了可能性。[42]然而,这种转变并不是对现有秩序的绝对拒绝,因为这只会导致新秩序的建立。它比这要激进得多:它是对政治和法律话语的重新建立,以揭示其根源的暴力和无法无天,以及缺乏合法依据,从而使其容易被持续和不可预测的重新解释。这种揭露的逻辑——这是一种卓越的政治逻辑——可以应用于我们的政治现实,以揭露其局限性。这并不是要拒绝我们当代的政治话语,而是要重新解读和评价它们。例如,自法国大革命以来一直伴随着我们的关于解放奴隶的论述,不应该被拒绝,而应该重新表述。虽然启蒙人文主义的解放理想有可能成为一种支配性的话语——通过它对理性和道德范畴的本质化——但如果它能从本质主义的基础中解脱出来,并从根本上作为一个非本质主义的、构成性开放的政治能指重新建立,它也可以成为一种解放的话语。正如德里达所说:
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古典的解放理想更不过时了。我们今天不能试图取消它的资格,无论是粗鲁的还是老练的,至少不能不把它看得太轻,形成最坏的同谋。但在这些确定的司法领域之外——在大的政治规模上的政治化,在所有自私的解释之外……起初看起来像是次要或边缘领域的其他领域必须不断开放。[43]
有人可能会说,因为后结构主义放弃了人文主义项目,它剥夺了自己利用这种话语的政治伦理内容来理论抵抗统治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它把婴儿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了。另一方面,由于德里达并没有排除启蒙人文主义计划,他也没有否定其话语中所包含的解放可能性。激进政治也不应否认这些可能性。德里达建议,我们可以将解放的论述从本质主义的基础中解放出来,从而将其扩展到包括迄今为止被认为不重要的其他政治斗争。换句话说,关于解放的论述可以在结构上保持开放,这样它的内容就不再受其基础的限制或决定。例如,《人权宣言》可以扩大到包括妇女、性和少数民族,甚至动物的权利。[44]解放的逻辑在今天仍然有效,尽管形式不同,表现为不同的斗争。
权利问题反映了解构主义政治与古典革命政治的区别。这两种战略都有政治权利的概念和在这些权利基础上进行解放斗争的形式。不同的是,古典革命政治认为这些权利是基本的,并建立在自然法则中,而解构主义政治认为这些权利是根本的:换句话说,这些权利没有稳定的基础,因此,它们的内容没有前缀。这使得它们可以接受多种不同的政治表述。解构主义的分析质疑自然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例如,德里达在他对自由社会契约理论的批判中认为,这些“自然”权利实际上是通过社会契约随意构成的,因此,它们不能声称是自然的。[45]于是,这些权利从社会领域转移到了自然领域,社会从属于自然,就像文字从属于言论一样。正如德里达在他对卢梭的批判中所主张的那样,社会是对自然人身份的威胁,同时也是必要的:自然人权利的思想只能通过契约来论述。权利不存在纯粹的自然基础,这使得它们有可能被改变和重新解释。它们不能再被铭刻在人类的本质中,因此,不能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它们没有坚实的基础,就不能总认为它们会继续存在。必须为之而战,在这个过程中,这些斗争将重新塑造它们。
德里达的安那其
正是通过这种解构逻辑的形式,政治行动才变得无政府(an-archic)。无政府行动在这里与古典无政府主义政治——克鲁泡特金和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区别开来,后者是由人类本质或理性等原始原则所支配的。虽然无政府主义的行动受到某些原则的制约,但它并不一定受这些原则的决定或限制。“无政府行动”是一种解构主义策略的可能结果,这种解构主义策略旨在破坏各种政治和哲学话语的形而上学权威。Reiner Schurmann将无政府行为定义为没有“为什么”的行为。[46]然而,对“安那其”(an-archy)的解构概念可能有些不同:它可能被视为带有“为什么?”——也就是说,行动被迫为自己解释和质疑自己,不是以创始原则的名义,而是以它已经开始的解构主义事业的名义。换句话说,一个无政府的行为是被迫为自己负责的,就像它迫使权威为自己负责一样。正是这种自我反省使得政治行动能够抵制权威,避免成为权威所反对的东西。所以这个无政府主义(an-archism)的概念可以被看作是激进的政治,使它意识到本质主义者和潜在的支配可能性,在它自己的话语。此外,通过上述的一些解构运动和策略,无政府主义(an-anarchism)寻求将激进政治从必然限制它的本质主义类别中解放出来。德里达对西方思想中仍然存在的权威和等级制度的揭露,以及他对对抗它们的各种策略的概述,使这种无政府(an-archist)式的干预成为可能。
德里达在激进想象中占据了许多关键的领域,并对反独裁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通过对话语中心主义文本权威的揭示和解构,德里达允许我们用同样的逻辑对基于这种权威的当代政治制度和话语进行批判。他还向我们表明,没有任何身份是纯粹和封闭的——它总是被它所排斥的东西所污染。这削弱了对立政治,因为身份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它所反对的东西构成的。更重要的是,通过德里达采用的各种解构主义策略和行动,他允许我们审视权力位置的微妙而有害的逻辑——激进政治重申其试图推翻的权威的倾向。他指出了激进政治的两种可能策略——倒置和颠覆——的局限性,表明它们都以重申威权结构和等级制度而达到顶峰。也就是说,他们都是权力地位逻辑的受害者。这些策略是将激进政治理论串起来的两个极端。然而,德里达展示了一种超越这种僵局的方法,将颠覆和倒置、肯定和绝对的拒绝交织在一起,以一种重新评估这些术语的方式,从而取代权力地位。通过这样做,他超越了后结构主义的问题,保留了人作为他自己的限制——让他的构成开放给激进的外部。这种通过内部的限制——哲学和政治的限制——构建的外部概念是任何理解政治的核心。它构成了正义和解放的政治道德层面,在法律和权威的限制下发挥作用,揭露其隐藏的暴力,并破坏以暴力为基础的机构的稳定。因此,德里达的政治思想可以被视为一种无政府主义,一种对权威的拷问,一种甚至质疑其自身基础的政治伦理策略,并迫使我们重新评估我们当代政治现实的局限性。
麦考瑞大学社会学系,悉尼,澳大利亚
[1] Christopher Norris, Derrida (London: Fontana Press, 1987), p. 19.
[2] ibid., p. 31.
[3] Jacques Derrida, Dissemination, trans. Barbara Johnson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1), p. 148.
[4] Jacques Derrida, Spurs: Nietzsche’s Style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p. 81.
[5] See Alan D. Schrift, ‘Nietzsche and the Critique of Oppositional Thinking’, 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 11 (1989): 783–90.
[6] Friedrich Nietzsche, Beyond Good and Evil, trans. R. J. Hollingdale (Harmondsworth, Mx: Penguin, 1990), p. 65.
[7] Jacques Derrida, ‘The Ends of Man’, in The Margins of Philosophy, trans. A. Bass (Brighton, UK: Harvester, 1982), p. 116.
[8] ibid., p. 128.
[9] Michel Foucault,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New York: Vintage, 1973), p. 386.
[10] Derrida plays upon this idea of spectre or ‘spirit’. See Jacques Derrida, Spectres of Marx: the State of Debt, the Work of Mourning & the New International, trans. Peggy Kamuf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p. 120–1.
[11] Rodolphe Gasché, The Tain of the Mirror: Derrida & the Philosophy of Reflec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19.
[12] Derrida, ‘The Ends of Man’, p. 135.
[13] ibid.
[14] Derrida says that this style of deconstruction is the one that ‘dominates France today’. See ibid.
[15] Alan D. Schrift, ‘Foucault and Derrida on Nietzsche and the End(s) of “Man”’, in Exceedingly Nietzsche: Aspects of Contemporary Nietzsche-Interpretation, ed. David Farrell Krell and David Wood (London: Routledge, 1988), p. 137.
[16] ibid., p. 138.
[17] ibid.
[18] ibid., p. 145.
[19] ibid.
[20] Derrida, The Margins of Philosophy, p. 18.
[21] ibid., p. 22.
[22] See Gasché, Tain of the Mirror, pp. 147–54.
[23] ibid., p. 152.
[24] ibid., p. 150.
[25] Jacques Derrida, Speech and Phenomena, and Other Essays on Husserl’s Theory of Signs, trans. David Allison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158.
[26] Rodolphe Gasché, Inventions of Difference: On Jacques Derrida(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 28.
[27] Jacques Derrida, Of Grammatology, trans.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24.
[28] ibid., p. 135.
[29] Jacques Derrida, Positions, trans. Alan Bass (London: Athlone Press, 1981), p. 12.
[30] See Michael R. Clifford, ‘Crossing (out) the Boundary: Foucault and Derrida on transgressing Transgression’, Philosophy Today 31 (1987): 223–33.
[31] ibid., p. 230.
[32] See John Lechte, Fifty Contemporary Thinkers: from Structuralism to Postmodernity (London: Routledge, 1994), p. 117.
[33] Derrida, Positions, p. 6.
[34] See John Caputo’s ‘Beyond Aestheticism: Derrida’s Responsible Anarchy’, Research in Phenomenology 18 (1988): 59–73.
[35] Richard Kearney, ‘Derrida’s Ethical Re-Turn’, in Working Through Derrida, ed. Gary B. Madison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30).
[36] Jacques Derrida, ‘Force of Law: The Mystical Foundation of Authority’, Deconstruction & the Possibility of Justice, ed. Drucilla Cornell et al.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p. 3–66 (p. 14).
[37] ibid.
[38] ibid., p. 37.
[39] ibid., p. 23.
[40] ibid., pp. 22–3.
[41] ibid., p. 27.
[42] ibid.
[43] ibid., p. 28.
[44] ibid.
[45] Michael Ryan, ‘Deconstruction and Social Theory: the Case of Liberalism’, in Working Through Derrida, ed. Madison, p. 160.
[46] Reiner Schurmann, Heidegger on Being and Acting: From Principles to Anarchy, trans. Christine-Marie Gros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