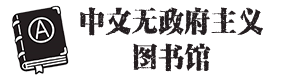伦佐·诺瓦托雷
超越两种无政府主义
自由意志共产主义者的社会政治概念所散发出的充满革命活力的社会思想,突破了人类痛苦的普遍深度,以一种近乎一元论的拥抱,与无政府个人主义的更高、更广泛的心理精神概念交织在一起,向往最终的、激进的无政府主义。
但是,无政府主义是与无限理念完全和谐的“最终的绝对”,而共产主义是流入经济经验主义的“相对的”社会的、法律的通道——因此是序曲和承诺,而不是完全的音乐和谐和史诗般的结局——碰巧,两种社会发展理论流派的蓬勃发展的孩子们继续争吵,仍然相互争斗——时而狂暴,时而平静——这是纯粹无政府主义的哲学精神遗产。这是古老的二元论,它再次披上了明显的逻辑外衣,仍然在恶性循环中打转,教条和乌托邦的旋转木马在不祥的理想轮轴上旋转,真理扭曲了它,生活美化了它。
正是从这种两部分都不敢大胆逃离的恶性循环中,我想果断地解放自己,让自己沉浸在新太阳的沐浴中。
渴望共产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渴望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者没有注意到,他们被阉割的社会学和人文主义的枷锁紧紧地抓住了,人文主义是一种个人非意志和伪基督教道德的虚伪的混合物。
任何接受社会、集体和人类事业的人,都不是处于人类中心主义不可同化者和否定者的自由、纯洁和原始本能的纯粹无政府状态。
我——无政府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不想也不能接受无神论共产主义的事业,因为我不相信群众的至高无上的崇高,因此我拒绝把无政府主义理解为人类共同生活的一种社会形式。
无政府主义存在于自由的精神中,存在于伟大的反叛者的本能中,存在于伟大而卓越的思想中。
无政府主义是被误解的独特性的最内在的充满活力的奥秘,因为孤独而强大,因为有孤独和爱的勇气而高贵,因为蔑视平凡而高贵,因为反对一切而英勇……
无政府主义是精神自我的甘露,而不是集体的社会学酒精。
无政府主义者是一个拒绝一切理由的人,因为他从内心的精神强度中散发出生命的快乐。
———
没有未来,没有人性,没有共产主义,没有无政府主义值得我牺牲生命。从我发现自我的那
一天起,我就把自己看作是最高的目标。
现在我把自己包裹在解放和解放的精神的上升轨迹中,我摆脱了本能的纯粹赤裸,翱翔在理想的社会学灵感之上——它将两个苍白的理想无政府主义的教条乌托邦主义联系在一起,以赞美——在风的冲突和太阳的盛宴之间——自我中心和强大的领主。
越过尼采笔下超人的悲剧性桥梁,我看到了一座更自由、更闪耀着磷光的峰顶,在那里,从来没有神人庆祝过他的出生或复活。
在人与人性之外,荒诞而崇高的神秘是不确定的、独特的生命与悸动。
我这疯狂的人类雄鹰,在这漆黑的夜晚,在思想的风暴怒号,思想的狂风怒吼的地方,一闪而过,越过黎明最早的微光的怀抱,在正午太阳的熊熊火焰中翱翔,感觉到自己在充满活力的、非道德的本能的淫荡的、酒神的悸动中,在那里,精神的光芒和情感的激情陶醉在野性的、纯洁的血与肉的泉源中。
———
快乐首先是一种感受生活的特殊方式。
对于感觉高尚的人来说,有从悲伤中获得的崇高喜悦和从快乐中获得的深沉忧伤。查拉图斯特拉,通过痛苦和崇高的孤独的山峰,热切地寻求知识的强烈喜悦,遇到了疯狂的,神圣的疯狂;朱尔斯·博诺(Jules Bonnot)通过《罪恶》(Crime)和《越界》(Transgression)歌颂了独一无二的意志,超越了善恶,升入了生死的英雄艺术的天空;布鲁诺·菲利皮在巨大的努力中被消灭,他主张“我”的权利反对虚伪的资产阶级和平民集体的社会约束;他们是璀璨的宝石,构成了我生命中非道德主义的自由主义花环,也是我精神悲剧的主角。
在生活中,我寻求精神上的快乐和本能上的奢侈享乐。我也不想知道这些邪恶的根源是在善的洞穴里还是在邪恶的漩涡深渊里。我站起来,如果在站起来的过程中遇到命运的悲惨闪电,生与死就会在我扭曲的嘴唇上弯曲,随后随我进入最高的混乱,在那里,艺术赞美那些被误解的坚强的反叛者,他们受到道德的辱骂和谴责,被科学称为疯子,被社会诅咒。
因此,我是欢欣鼓舞的解放了的本能。侧耳倾听自己,我听到了我的解放精神的雷鸣般的嚎叫,它唱着最后胜利的史诗般的胜利之歌。
所有界限都被打碎了。现在我爱我自己,我高举我自己,我歌唱我自己,我赞美我自己。我的旧梦在女人苍白芬芳的皮肤上得到了安息。我那充满激情的、异教的思想是一个不羁的诗人的思想,在他们乖张的眼睛里,在欢乐和邪恶的灵魂跳着最疯狂的舞蹈的地方,我的思想是情欲的反映。只有星星的闪烁,河流的流动,森林的窃窃私语,才能说明我内心的东西。谁听不懂大自然奇妙的交响乐,谁就听不懂我那动人的诗句。
———
自我不是一种思想或理论,而是一种心态,一种特殊的感受方式。当我觉得有必要果断地释放我的半人马和狂暴的种马时,我周围就会出现爱与血的疯狂狂欢,因为我是——我感觉到了——社会道德沼泽里的居民所说的“普通罪犯”。
———
疯子吗?随你的便!正常人从来没有得到过我的爱。在人类中,我最爱的是思想和行动的“罪犯”(艺术家、小偷、流浪汉、诗人)。
在女人中,我喜欢变态。我喜欢他们在傍晚的夕阳下穿着蓝色的衣服。我爱他们穿着红色的衣服,站在即将到来的黎明的金色光芒中;我爱他们赤裸裸地躺在爱的床上,我爱他们穿着白色的衣服躺在死亡的小床上。
我可怜的,矮小的,伟大的姐妹我一直爱着她们,却从未拥有过她们。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告诉我,哦,我活着的姐妹们,哦,我死去的姐妹们:谁?你们当中谁是最有名的,最伟大的,最变态的?
啊,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
克拉拉,是你!但你现在在哪里?
我曾经通过奥克塔夫·米尔博的《邪恶花园》认识你。我了解你,我爱你!你是最奇特、最精致的生物,最浪漫、最具人性、最残忍的人,你懂得在受尽折磨的呻吟和花香中敏锐地感受生活,敏锐地感受爱。每当我想到你在金色黄昏的金色前奏下,疯狂而轻快地奔跑着,去寻找被鲜血染红的绿草皮,用它为自己做一张结婚的床,给自己一个最深沉的爱的拥抱,我对你的钦佩使我感到无比兴奋。
啊,浪漫而优雅的生物,你如何能够穿透花朵的神圣奇迹,中国草甸的芬芳如何教会你升华....
只有大色狼和大变态才能像你一样,在受折磨的人凄厉可怕的哭喊声中听到本能的强烈而有力的声音:“爱你自己!爱自己!让你自己也像花儿一样……事实上,只有爱!”我能理解,我能感觉到,克拉拉,你那邪恶而不道德的爱,被阉割了的纯洁的贞洁和男人的道德所诅咒和憎恶。我感觉到它是如何从本能的最深处,疯狂而冲动地迸发出来,在人类牺牲的残酷和野蛮景象面前,以热情和神秘的音乐般的和谐,无拘无束地、壮丽地传播开来,并庆祝最痛苦的最深刻的快乐的最高和最有力的悸动,在最充实、最悲惨的生命的流血的心灵中共鸣。
———
哦,奥克塔夫·米尔博(Octave Mirbeau)里乖戾的女主角,我赞美你,歌颂你,因为我是邪恶的野蛮歌手。
在理性与善的两种无政府主义之上——光荣而胜利地——我举起了本能与恶的无政府主义的旗帜。